日头爬到头顶时,姜知微坐在济世堂废墟的断墙上,手里攥着半块捡来的药杵。
木头被水泡得发胀,表面的包浆被冲得斑驳,露出里面浅黄的纹路。
这是祖父用了三十年的药杵,当年父亲还在时,总爱抢着用它捣制甘草,说“这杵子有灵性,捣出的药格外匀”。
如今它斜斜地卡在两块断砖之间,像是从泥里挣扎着探出来的一截希望。
“还能凑合用。”
姜明远蹲在瓦砾堆里,把找到的铜药碾零件往麻袋里装,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找个木匠修修,还能捣药。”
许春娥正用一块破布擦着几本泡得发胀的旧账本,纸页黏在一起,字迹晕成了一团蓝黑。
“你看这页。”
她指着其中一页对姜知微笑,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泥。
“去年三月,张屠户家小子惊风,欠的那贴牛黄散,到现在还没还呢。”
姜知微也跟着笑,喉咙却发紧。
她低头看向掌心,药杵的潮气透过指尖渗进来,凉丝丝的,像此刻胸口的玉佩。
那点昨夜的暖意彻底散了,只剩下玉石本真的、近乎砭骨的凉,贴在衣襟上,像一块被遗忘的冰。
“累不累?”
许春娥挪过来,把一个用荷叶包着的窝头递过来,“胡三姑刚蒸的,掺了点玉米面,你垫垫肚子。”
姜知微接过窝头。
指尖碰到祖母的手,才发现她的指关节肿得发亮,虎口处还有道被木刺划破的口子,血珠混着泥水凝在上面。
“祖母,你的手。”
她赶紧放下窝头,从怀里摸出块干净的布条,这是昨夜高坡上妇人给的,她一直贴身揣着。
“没事,小口子。”
许春娥想缩回手,被姜知微按住了。
小姑娘的手指纤细,动作却稳当,用干净的角落蘸了点随身携带的烈酒,轻轻擦过伤口,再用布条仔细缠好。
“疼吗?”她抬头问,眼里映着日头的光,亮得像含着水。
“不疼。”许春娥拍拍她的手背,“你这手艺,比你娘当年还细。”
提到母亲,两人都沉默了。
姜知微低头咬了口窝头,粗糙的玉米碴刺得嗓子疼,却嚼出了点微甜。
她忽然想起昨夜那道墨发深衣的身影,想起那双琉璃般的眼,还有玉佩上流转的白光。
是真的有过吗?还是伤势太重,脑子糊涂了?
正想着,太阳穴忽然突突地跳了两下。
不是疼,更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轻轻撞了撞,带着点懵懂的、怯生生的力道。
紧接着,一道极淡的感受漫了过来,像投入湖面的石子,荡开一圈模糊的涟漪。
“冷”
姜知微猛地停住咀嚼,差点把窝头咽错了嗓子。
她眨了眨眼,以为是风声。
可那道感受又清晰了些,不是声音,更不是念头。
而是一种纯粹的、带着茫然的感知,像初生的幼兽在试探周遭的温度。
“谁?”她下意识地在心里问。
没有回应。
只有那道“冷”的感受还在,混着点微弱的慌,像迷路的孩子找不到方向。
姜知微的心跳漏了一拍。
她悄悄摸向胸口的玉佩,冰凉的玉面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轻轻颤动,比昨夜的悸动更微弱,却更真切。
是玉佩吗?是那块母亲留下的、陪着她走过三年孤苦日子的玉佩?
“知微?发什么愣呢?”
姜明远扛着麻袋走过来,额头上的汗顺着皱纹往下淌。
“李阿牛说前面王秀才家的厢房还能住,咱们先去落脚,晚了怕被别人占了。”
“哦,好。”
姜知微赶紧应着,把剩下的窝头塞进怀里,扶着许春娥站起来。
她的腿还有点软,走了两步,那道“冷”的感受又冒了出来,这次还多了点别的。
“暖?”
这道感知指向她的手心,指向她扶着祖母的那只手。
姜知微低头看去,自己的手温乎乎的,沾着点窝头的碎屑和泥土,再平常不过。
可那道感知却像找到了热源,微微往这边靠了靠,带着点依赖似的。
她心里忽然冒出个荒唐的念头:难道是那块玉?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她按了下去。
玉怎么会有感知?怎么会觉得冷、觉得暖?定是伤还没好利索,才会胡思乱想。
可那道感知却没消失。
一行人跟着李阿牛往王秀才家走,路上要蹚过几段没退尽的积水。
水没过脚踝,冰得刺骨,姜知微打了个寒颤,那道感知也跟着“抖”了一下,比她的寒颤更怯,像被冻着了的小猫。
“冷”它又“说”了一声。
姜知微咬着唇,没敢再想。她加快脚步跟上祖父,目光扫过路边的废墟。
周大勇的铁匠铺塌了一半,铁砧子斜插在泥里,还冒着点锈。
黄四娘的茶摊只剩个破木桌,上面还沾着没冲净的茶渍。
柳青萝的书坊更惨,书页泡在水里,像一群惨白的蝴蝶
每个人都在失去,每个人也都在扛着。
王秀才家的厢房在镇子最东头,是间朝南的小屋,万幸没被洪水淹到,只是窗纸破了大半,风呼呼地往里灌。
李阿牛已经帮着扫干净了,还找来几块木板挡在窗上,勉强能住人。
“先凑合一晚。”
姜明远把麻袋放在墙角,“明天我去山上砍点柴,把炕烧起来,就暖和了。”
许春娥开始整理带来的东西。
几件换洗衣物、半包没受潮的糙米、还有姜知微抢出来的那本《姜氏本草》。
她把书小心地摊在桌上,一页页地分开,对着日头晾晒,动作轻柔得像在呵护初生的婴儿。
姜知微坐在炕沿上,看着祖父母忙碌的身影,心里那道感知又活跃起来。
它不再说“冷”了,似乎被屋里的人气烘得安稳了些,偶尔会轻轻“碰”一下她的意识,像在确认她是否还在。
她试着在心里想:“你是谁?”
那道感知顿了顿,似乎在努力理解这个问题。过了好一会儿,才传回一道更模糊的感受,像隔着厚厚的棉絮。
“在。”
只是“在”?姜知微皱起眉。她又想:“你在什么地方?”
这次的回应快了些,那道感知轻轻“指”了指她的胸口。
姜知微的心跳彻底乱了。
她猛地低头,攥住衣襟下的玉佩,冰凉的触感透过布料传来。是它,真的是它。
这块母亲留下的玉佩,不知怎么,竟有了一道懵懂的意识,像个刚出生的娃娃,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自己“在”,知道“冷”,知道“暖”。
为什么?
是因为那场洪水?还是因为昨夜那道身影?
她不敢深想,却又忍不住好奇。
她用指尖轻轻摩挲着玉佩的轮廓,在心里想:“你是不是昨晚那个人?”
那道感知似乎愣了一下,没明白“人”是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儿,传回一道极淡的、带着困惑的“光”,像是在说,它和那道白光有关。
姜知微的呼吸慢了下来。她忽然不怕了。
不管这道意识是什么,它没有恶意,甚至还带着点依赖,像只被雨水打湿的小兽,怯生生地依偎着她。
就像,就像当年爹娘刚走时,她抱着这块玉佩在被窝里哭,总觉得玉里藏着娘的影子。
“以后我叫你什么?”她在心里轻声问。
那道意识没回应,似乎还不明白“叫什么”的意思。
它只是轻轻“靠”了过来,带着点安稳的、像被晒过的被褥般的暖意,这次不是玉的暖,是意识本身的温度。
姜知微笑了笑,指尖在玉佩上轻轻敲了敲。
窗外的风还在吹,带着雨后的凉意。
屋里,祖父在修补漏风的门板,祖母在翻晒医书的纸页,发出沙沙的轻响。
墙角的麻袋里,药杵和铜药碾的零件偶尔碰撞,发出细碎的叮当声。
一切都碎了,又好像都还在。
姜知微靠在墙上,看着这一切。
胸口的玉佩依旧冰凉,可那道藏在玉里的意识,却像一颗刚埋下的种子,带着微弱的生机,在她心里扎下了根。
她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知道这道意识会带来什么。
可此刻,听着祖父母的动静,感受着那道怯生生的“存在”,她忽然觉得,天塌下来,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
日头渐渐西斜,把厢房的影子拉得很长。
姜明远修好了门板,许春娥把医书叠得整整齐齐,姜知微则把那半块药杵放在窗台上,让最后一点日头照着它。
晚饭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就着剩下的窝头。
三人围坐在小桌旁,谁都没多说话,却吃得格外安心。
夜深时,姜知微躺在临时搭起的铺盖上。
听着祖父的鼾声和祖母轻微的咳嗽,胸口的玉佩贴着心口,那道意识安静地“待”着,像个熟睡的娃娃。
她闭上眼睛,终于不再想昨夜的身影,不再想玉佩的秘密。
只要人还在,家就还在。
哪怕只是一间漏风的厢房,哪怕只有半块药杵,只要他们祖孙三个在一起,就总能把日子过下去。
至于那道藏在玉里的意识,等天亮了,再慢慢弄明白吧。
窗外的月亮又出来了,透过木板的缝隙,洒下几缕清辉,落在窗台上的药杵上,泛着淡淡的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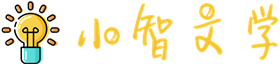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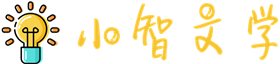 小智文学
小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