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青藤街的暖阳》由麦冬1234所撰写,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也是一部良心年代著作,内容不拖泥带水,全篇都是看点,很多人被里面的主角周明远所吸引,目前青藤街的暖阳这本书写了150140字,完结。
青藤街的暖阳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青藤街的晨光总带着股湿漉漉的凉意。当东边的天际刚泛起鱼肚白时,周明远已经踩着露水推开了“暖阳杂货铺”的木门。门轴转动的“吱呀”声划破了老街的寂静,惊得屋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在灰蒙蒙的天空中盘旋两圈,又落回对面斑驳的墙头上,歪着头打量这个早起的老人。
门口的木板还歪歪扭扭地贴着,是林小满昨天傍晚匆匆钉上去的。少年用彩色粉笔写的“这是周叔的家,不许拆”几个字,被夜里的露水打湿,晕成了一片模糊的色块,却依旧倔强地挡在刺眼的红“拆”字上。周明远伸手摸了摸木板边缘,粗糙的木纹上还留着少年指甲抠过的痕迹,想来是昨晚钉木板时太用力,指尖都磨红了。
他弯腰清扫台阶上的落叶,竹扫帚划过水泥地,发出“沙沙”的轻响。扫帚柄上裹着层防滑的布条,是林慧生前缠的,布条已经洗得发白,露出里面磨得光滑的竹节。“当年你总说我扫地太用力,把扫帚都用坏了。”周明远对着空无一人的门口轻声说,仿佛妻子还站在那里,笑着看他笨拙的样子。
杂货铺里弥漫着熟悉的气息,是老木头、旧纸张和淡淡煤烟混合的味道。周明远走到柜台后坐下,从抽屉里拿出那只玻璃罐,里面装着街坊孩子们留下的宝贝:弹珠、羽毛、褪色的糖纸……他把昨天林小满留下的玻璃珠放进去,透明的珠体在晨光中折射出细碎的光,和其他珠子碰撞时发出清脆的“叮咚”声,像极了林慧挂在窗边的风铃。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指针刚过六点。这钟是1995年街坊们凑钱买的,钟面上的“喜鹊登梅”图案已经磨得模糊不清,却依旧走得精准。周明远记得买钟那天,林慧特意煮了一大锅红豆汤,全街的人都挤在铺子里,边喝汤边看他挂钟。周磊那时候才十岁,踮着脚尖非要亲手拧上发条,结果手一滑,钟摆磕在柜台上,磕出个小小的凹痕——现在那个凹痕还在,像时光留下的印记。
他起身去生煤炉,铁皮煤炉早就被烟火熏成了深褐色,炉门上的铁锈像片细密的蛛网。周明远往炉膛里添了几块蜂窝煤,划着火柴引燃纸团,橘红色的火苗“噼啪”地舔舐着煤块,渐渐窜起跳跃的火焰。他蹲在炉边烤手,火光映在脸上,驱散了些许寒意,也照亮了眼角深深的皱纹。
“周叔,又起这么早啊!”对门的李奶奶挎着菜篮子走过,看见周明远在生炉子,隔着街喊了一声,“我刚从早市回来,给您捎了几个热包子!”她快步走进来,把油纸包着的包子放在柜台上,热气透过纸张渗出来,带着葱花和肉馅的香气,“猪肉大葱馅的,您最爱吃的。”
周明远接过包子,指尖触到滚烫的油纸,暖意顺着指尖蔓延到心口。“李婶,总让您破费。”他笑着推辞,却还是拿出个搪瓷盘,把包子一个个摆好。这盘子是林慧当年在学校得的奖品,边缘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里面银灰色的铁皮,盘底印着的“先进工作者”字样已经模糊不清。
“跟我客气啥!”李奶奶拍了拍他的胳膊,看见柜台上的玻璃罐,眼睛一亮,“这不是小满那孩子的玻璃珠吗?这孩子看着闷不吭声,心思倒细。昨天我看见他在街角捡弹珠,冻得手都红了,说是要给您串个风铃。”
周明远的心轻轻一动。他想起昨天那个抱着饼干狼吞虎咽的少年,想起他攥着玻璃珠时警惕又不安的眼神,想起他贴木板时冻得发紫的鼻尖。这孩子像株在石缝里挣扎的野草,看着倔强,实则脆弱得很。
李奶奶坐了会儿就回去忙了,临走前又叮嘱:“拆迁队要是再来捣乱,您就喊一声,咱街坊们都在呢!”周明远送她到门口,看见晨光已经铺满了青藤街,给老旧的屋顶和斑驳的墙壁镀上了层金边。街角的老槐树上,几个麻雀正叽叽喳喳地啄着残留在枝丫上的野果,一切都和往常一样,仿佛墙上的红“拆”字只是场噩梦。
他回到铺子里,刚咬了口包子,就听见门口传来轻轻的响动。抬头一看,林小满背着个洗得发白的书包,低着头站在门槛边,脚尖在地上蹭来蹭去,像是做错事的孩子。少年穿着件不合身的旧校服,袖口磨得开了线,裤脚沾着干涸的泥渍,头发乱糟糟的,额前的碎发遮住了眼睛。
“进来吧,外面冷。”周明远朝他招手,声音放得很柔。林小满犹豫了一下,还是挪着步子走进来,书包带子滑到了胳膊上,他慌忙往上提了提,露出手腕上一道浅浅的疤痕,像是被什么东西划伤的。
“还没吃饭吧?”周明远把装包子的搪瓷盘推到他面前,“快吃,热乎着呢。”林小满捏着书包带子,小声说了句“谢谢”,却没动筷子,眼睛偷偷瞟向货架最上层。那里摆着个旧款的奥特曼玩偶,是周磊小时候的宝贝,蓝色的胳膊断了一只,却被缝补得整整齐齐。
周明远看在眼里,起身把奥特曼拿下来递给他:“喜欢就拿着玩,这是周叔儿子小时候的玩具。”少年的眼睛瞬间亮了,像被点燃的星火,却又猛地低下头:“我不要,会弄脏的。”他的手指在裤缝上蹭了蹭,那里沾着黑乎乎的油污。
“脏了能洗,玩具就是给孩子玩的。”周明远把奥特曼塞进他怀里,“你看它胳膊断了,正好需要人陪呢。”林小满抱着玩偶,指尖轻轻碰了碰奥特曼断了的胳膊,忽然小声说:“我……我能修好它。”
“哦?你会修东西?”周明远有些意外。林小满点点头,从书包里掏出个铁皮盒,盒子边角都磨圆了,上面印着褪色的卡通图案。他打开盒子,里面整齐地放着些磨得发亮的小工具:螺丝刀、小钳子、几卷细铁丝,还有半包不同型号的螺丝,甚至还有个小小的放大镜。
“这些是我爷爷的。”林小满拿起一把迷你螺丝刀,手指轻轻摩挲着金属柄,“他以前是修钟表的,总带着我在他的修表摊旁玩,教我怎么拆零件、怎么组装。”少年的声音低了下去,“他走后,我就把这些工具带在身上,想他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周明远看着那些小巧的工具,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他小时候总蹲在父亲的修表摊旁,看父亲用镊子夹起比米粒还小的零件,父亲总说:“修东西和做人一样,得有耐心,不能急,零件再小也有它的用处。”后来他把这手艺用到了杂货铺里,修闹钟、收音机、自行车……没想到几十年后,会在一个陌生少年身上看到熟悉的影子。
“那你试试?”周明远把针线筐递给他,里面有林慧留下的各色线团和几根粗细不一的针。林小满抱着奥特曼走到煤炉边,小心翼翼地拆开缝合的地方,用细铁丝把断了的胳膊固定好,又选了根米色的线,笨拙却认真地缝了起来。
他的动作不算熟练,手指甚至有些发抖,却异常专注。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低垂的眼睫上,投下小小的阴影,额前的碎发被汗水濡湿,贴在光洁的额头上。周明远坐在柜台后看着他,忽然觉得这画面有些熟悉——很多年前,周磊也是这样蹲在煤炉边,看他修闹钟,小小的手指学着他的样子捏着螺丝刀,嘴里还念念有词:“爸爸,这个零件是不是像奥特曼的心脏?”
“周叔,您看!”林小满举着修好的奥特曼,眼睛亮晶晶的。玩偶的胳膊虽然还能看出修补的痕迹,却稳稳地立着,像是重新有了生命力。周明远接过玩偶,轻轻碰了碰缝合的地方,线脚虽然歪歪扭扭,却缝得很结实。
“真厉害!比周叔年轻时缝得还好。”周明远由衷地赞叹。林小满被夸得脸通红,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嘴角却忍不住向上扬。周明远看着他害羞的样子,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小满,你要是不嫌弃,以后常来铺子坐坐怎么样?周叔教你修东西,你帮周叔看看铺子,咱们互相帮忙。”
林小满猛地抬起头,眼里满是不敢相信,像是听到了天大的好消息。“真的吗?”他的声音带着颤抖,“我……我不要工钱,管饭就行。”周明远被他认真的样子逗笑了:“管饭,顿顿有肉!不过你得答应我,每天去学校上学,不能再在街上游荡了。”
少年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眶红得像兔子。他低下头,用袖子偷偷擦了擦眼睛,怀里的奥特曼玩偶被抱得更紧了,像是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临近中午时,杂货铺的风铃忽然响了。那是串用旧钥匙和铁片做的风铃,是周磊十岁时的手工课作业,挂在门口十几年,风吹过时总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周明远抬头,看见老邮递员赵叔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慢悠悠地停在门口。
赵叔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绿色邮递员制服,帽子歪戴在头上,车后座的绿色邮包里塞着几封信,车把上还挂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周老哥,有你的信!”他把自行车支在门口,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走进来,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瞬间散开,“今儿这风刮得邪乎,冻得我鼻子都快掉了。”
周明远赶紧给赵叔倒了杯热茶,接过他递来的信件。信封已经泛黄,边缘磨损得厉害,邮票也有些褪色,上面印着一朵小小的栀子花。收信人写着“青藤街暖阳杂货铺 周明远收”,字迹清秀有力,带着点女孩子特有的娟秀。
“这信可不一般,压在邮局仓库的旧信件堆里了。”赵叔捧着热茶暖手,话匣子打开了,“昨天局里整理旧档案,从角落里翻出来一箱子没送出去的信,这封就是其中之一。看邮戳像是十年前的,估计是寄信人地址写错了,辗转了这么久才到你手上。”
周明远摩挲着信封,总觉得这字迹有些眼熟。他小心地拆开信封,里面是张折叠的信纸,展开后,一股淡淡的薰衣草香气飘了出来——是林慧最喜欢的味道。他的心跳忽然漏了一拍,目光落在信纸上的落款处:苏晓棠。
“苏晓棠……”周明远喃喃地念着这个名字,尘封的记忆忽然被打开。那是十几年前住在街尾的女孩,父母离婚后跟着奶奶住,奶奶去世后就被外地的亲戚接走了。那孩子总爱蹲在杂货铺的柜台旁写作业,扎着两个羊角辫,眼睛像黑葡萄一样亮。林慧常给她留着热牛奶,周磊则把自己最宝贝的弹珠分一半给她玩。
信里的字迹娟秀工整,写满了三页纸。苏晓棠说她在外地过得很好,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建筑设计,说她总想起青藤街的日子:想起周叔修闹钟时认真的样子,爷爷的老座钟就是周叔修好的;想起林慧阿姨烤的红薯,冬天揣在怀里暖乎乎的;想起周磊哥哥教她打弹珠的夏天,阳光落在玻璃珠上,像撒了把星星。
“周叔,您还记得吗?我走的前一天,您给我装了满满一袋玻璃珠,说‘带着它们,就像带着青藤街的光’。”信里写道,“我把那些珠子串成了风铃,挂在宿舍的窗前,风吹过时,就像听见了青藤街的声音。等我学成了,一定回来给青藤街画张图,把这里的老房子、老槐树、您的杂货铺都画下来,永远留住它们。”
信纸的末尾夹着片干枯的青藤叶,叶脉清晰可见,边缘微微卷曲,却依旧带着淡淡的绿意。周明远捏着那片叶子,忽然想起苏晓棠走的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初冬的早晨,她背着书包站在门口,手里攥着这片青藤叶,说:“周叔,这叶子能留住春天,等我回来,咱们一起种青藤。”
“这丫头,心里一直记着青藤街呢。”周明远把信和青藤叶小心翼翼地夹进相册里,放在苏晓棠当年画的那张槐树图旁边。相册里还夹着很多老照片:有周磊满月时的照片,被裹在林慧的碎花衬衫里;有杂货铺开业时的合影,街坊们挤在门口笑得灿烂;还有周磊参军前的照片,穿着崭新的军装,站在货架前敬礼,背景里的搪瓷缸、旧算盘都清晰可见。
赵叔看着他的举动,叹了口气:“时间过得真快,晓棠那丫头现在都成大姑娘了。说起来,这青藤街要是真拆了,以后这些孩子回来,怕是连家在哪儿都找不到了。”他从车把上拿下布包,“对了,这是李婶给您捎的腌萝卜,说配粥吃香得很。”
周明远接过布包,萝卜的咸香混着薰衣草的清香,在铺子里弥漫开来。他走到门口,看见林小满正蹲在墙根下,用捡来的彩色粉笔在木板周围画满了小人:有举着锤子的自己,有缝补衣服的林慧,有敬着军礼的周磊,还有个扎羊角辫的女孩,手里举着片青藤叶。少年的鼻尖冻得通红,手指却灵活地舞动着,粉笔灰沾满了指尖。
“周叔,您看我画得像吗?”林小满抬头朝他笑,脸上沾着白花花的粉笔灰,像只调皮的小花猫。周明远走过去,看见少年还在每个小人的手里画了颗玻璃珠,阳光透过珠子,在墙上投下细碎的彩虹,那些小人仿佛活了过来,在斑驳的墙面上微笑、奔跑、招手。
赵叔拿出挂在脖子上的旧相机,这相机是他年轻时省吃俭用买的,镜头上还留着几处磕碰的痕迹。“咔嚓”一声,他按下快门,把这温暖的画面定格下来。“这张照片得洗出来,放在你这铺子里,比啥都珍贵。”他拍着周明远的肩膀说,“你看,只要还有人记得,还有人守护,这青藤街的暖光就灭不了。”
煤炉里的火越烧越旺,暖光映在每个人脸上。周明远看着墙上的粉笔画和玻璃珠的光,看着手里苏晓棠的信,看着林小满冻得通红却依旧明亮的眼睛,忽然觉得心里那块被“拆”字压着的石头,好像轻了许多。
他转身从货架上拿下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林慧生前攒的玻璃珠,红的、蓝的、透明的,一颗颗在阳光下闪着光。“小满,过来。”他把玻璃珠倒在柜台上,“这些给你,去把它们嵌在你的画里,让它们替我们留住光。”
林小满的眼睛亮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捡起玻璃珠,跑到墙边,把它们一颗颗嵌在粉笔小人的手里、衣服上、头发上。阳光透过玻璃珠,在墙上投下五颜六色的光斑,像撒了一地的星星。路过的街坊都停下脚步,看着这奇特的画面,有人回家拿来了更多的玻璃珠,有人找来彩色的粉笔,加入了画画的队伍。
很快,那面斑驳的墙壁就变成了一幅热闹的画卷:有孩子们在老槐树下跳皮筋,有街坊们在杂货铺门口包饺子,有周磊穿着军装敬礼的身影,还有林慧微笑着给孩子们分糖果……每一处都嵌着亮晶晶的玻璃珠,在阳光下闪烁着温暖的光,把刺眼的红“拆”字彻底淹没在这片光海里。
周明远站在门口,看着这突如其来的温暖,眼眶渐渐湿润。他知道,拆迁的威胁还在,困难也不会少,但只要这些温暖的碎片还在,只要大家的心还在一起,就一定能拼出个完整的春天。就像苏晓棠信里写的,就像林小满画的,就像这满墙的玻璃珠折射的光——青藤街的暖光,永远都不会灭。
门口的风铃又响了,这次的声音格外清脆,像是在唱歌。周明远抬头望向天空,青藤街的雾气已经散尽,阳光穿过光秃秃的树梢,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和几十年前一样,清澈又响亮。他仿佛看见林慧站在阳光里,笑着对他说:“明远,你看,春天总会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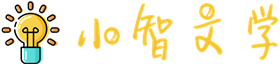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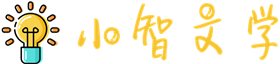 小智文学
小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