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一本引人入胜的历史古代小说,朕的大汉,容不得巫蛊,正在等待着你的发现。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让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奇幻与冒险的世界。作者暴走术士的精湛文笔和细腻描绘,更是为这本小说增添了不少色彩。目前,小说已经连载,让人热血沸腾。快来加入这场阅读盛宴,163599字的精彩内容在等着你!
朕的大汉,容不得巫蛊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九、廷争盐策
石渠阁的灯光亮至深夜,刘据案头木牍上的字迹,从潦草随记,逐渐演变成条分缕析的要点。他并未撰写完整的奏疏,那太过招摇,而是将“盐引策”的核心理念、可能的试点区域(重点标注河东)、运作模式框架、以及预期的利弊,以提纲挈领的方式整理出来。他需要这份东西,不是为了立刻呈送御前,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清晰、有力地陈述自己的观点。
机会,比他预想的来得更快。
就在石渠阁夜谈后的第三日,一次非正式的小型朝会上,议题偶然涉及了近来各地,尤其是关东郡国,因盐价问题引发的几起小规模民怨。起因不过是某位郡守例行公事般的奏报,提及需加强盐市监管,以防奸商囤积居奇。
龙椅上,一直闭目养神的汉武帝刘彻,忽然睁开了眼睛,目光扫过垂首侍立的群臣,最后落在了站在前列的太子刘据身上。
“太子。”皇帝的声音不高,却在寂静的大殿中异常清晰,“前番你与桑大夫所言‘盐引’之策,朕略有耳闻。今日既论及盐政,你且说说,若依你之策,当如何平息此类民怨,又能确保国用无缺?”
来了!
刹那间,宣室殿内所有目光,或明或暗,齐刷刷聚焦在刘据身上。他能感觉到桑弘羊投来的审视目光,卫青微微蹙起的眉头,以及无数朝臣眼中混杂的好奇、怀疑与审视。
他深吸一口气,压下骤然加速的心跳,上前一步,躬身行礼,声音沉稳:“回父皇,儿臣前番与桑大夫探讨,确有一些粗浅想法,旨在‘于不变中求变’,或可稍解盐政之困,为朝廷开源节流。”
他并未直接回答如何平息具体民怨,而是先定下基调——这是为了“朝廷”,为了“开源节流”。
“哦?于不变中求变?”汉武帝手指轻轻敲击着御座扶手,“细细道来。”
“诺。”刘据直起身,目光平静地扫过众臣,最后落回御座,“现行盐铁官营,乃桑大夫殚精竭虑所定,为北击匈奴立下汗马功劳,此乃不刊之论。”他先肯定现状,安抚桑弘羊及其背后势力。
“然,盐乃民生必需,不可或缺。官盐价高,或因运输损耗,或因吏治不清,致使民有怨言,私盐遂有可乘之机。强禁私盐,徒增官府稽查之耗,激化民怨,恐非长久之计。”
他点出问题根源,将矛头指向了“吏治”和“效率”,而非政策本身。
“儿臣愚见,或可效仿古之‘榷酤’(酒类专卖),但加以变通。择一盐产重地,如河东,试行‘盐引’新法。”他终于抛出了核心概念。
“所谓‘盐引’,即朝廷印制、发售之专卖凭证。商人纳钱(或以粮帛折价)于朝廷指定机构,购得‘盐引’,凭引至指定盐场,支取定额、定质之盐,再运销至指定区域。朝廷则坐收‘盐引’之款,此款可先于盐产出之前入库,利于国库周转。”
他清晰地阐述了“盐引”的基本运作模式,重点突出了“先收钱”和“定额定质”的优势。
“如此一来,其一,朝廷收入稳定且提前,不受运输损耗、吏治贪腐直接影响,此乃‘节流’。其二,引入商人运销,彼等为求利,必尽力减少损耗,提升效率,或可促使盐质改善,此乃间接‘开源’,亦可缓解民怨。其三,朝廷只需牢牢掌控‘盐引’印制发售、盐场生产源头及最终稽查之权,便可掌控大局,此乃‘不变’之根本。其四,此法若行,或可将部分试图铤而走险的私盐贩子,转化为合法纳课的盐商,化暗为明,减少治安之患。”
他将利弊一一剖析,逻辑清晰,尤其强调了对朝廷“利”的一面。
殿内一片寂静。许多官员脸上露出思索之色,显然被这新奇而又似乎具备操作性的想法所吸引。
“荒谬!”
一声冷斥打破了沉默。出言的并非桑弘羊,而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臣,乃是掌管刑名的廷尉,属于较为保守的官僚体系一员。“盐铁乃国之命脉,岂能假手商贾?此例一开,必致奸商猾贾操纵盐价,盘剥百姓,与民争利更甚!且商人重利轻义,如何能确保其不舞弊营私?此法看似精巧,实则动摇国本!”
刘据早有准备,从容应对:“老廷尉所虑极是。故而儿臣强调,朝廷需掌控源头与稽查。‘盐引’价格、发售数量、支盐地点,皆由朝廷核定,商人无权更改,何来操纵盐价?至于舞弊,正因引入商人,使其相互竞争,朝廷方能超然其上,严查不法。若盐吏贪腐,朝廷自查难免投鼠忌器;若商人舞弊,朝廷查办则名正言顺,力度更甚。此乃以商制吏,以明替暗。”
他巧妙地将“商人”可能带来的问题,转化为制衡“吏治”的工具。
那老廷尉一时语塞,脸色涨红。
此时,桑弘羊终于缓缓出列。他面色平静,对着御座躬身,然后转向刘据:“殿下高才,此‘盐引’之策,构思奇巧,臣亦觉有其可取之处。”
他先扬后抑,话锋随即一转:“然,正如廷尉所言,事关国本,不可不慎。臣有三问,请教殿下。一,盐引发售,如何定价?定高了,商人不愿买,徒成空文;定低了,朝廷利权流失,岂非得不偿失?二,指定区域销售,如何确保盐商不越界侵销,扰乱他处盐市?三,亦是关键,试行之初,若原有盐吏安置不当,激起变故,或商人联合抵制,又当如何应对?此皆关乎成败之细节,望殿下明示。”
桑弘羊不愧是实干家,问题直指核心操作层面,每一个都切中要害。
刘据心念电转,这些问题他虽有粗略思考,但远未完善。他不能示弱,也不能空谈,必须给出有说服力的方向。
“桑大夫所问,切中肯綮。”刘据保持镇定,“关于定价,或可参考往年盐利、生产成本、运输费用及民间承受力,由大农令牵头,会同相关郡守,核算出一基准价,并可尝试‘竞价’发售,价高者得,如此既可确保朝廷利益,亦显公平。”
他引入了“竞价”概念。
“关于销界,可在‘盐引’之上明确标注销售郡县,并建立严格的核验与稽查制度,跨界之盐,视为私盐,重罚不贷。同时,鼓励民间告发,查实重赏。”
“至于盐吏安置与商人抵制……”刘据略一沉吟,“试行之初,范围宜小,如仅限河东部分盐场。原有盐吏,可择优纳入新的监管体系,其余或调任,或给予补偿。至于商人……重利之下,必有勇夫。只要朝廷展现出推行此法之决心,并确保其合法利润,抵制者不过少数,成不了气候。”
他的回答虽未尽善尽美,但思路清晰,应对得当,尤其是“竞价发售”和“严格稽查配合民间告发”的想法,让不少官员暗暗点头。
桑弘羊目光微闪,不再追问,退回班列,淡淡道:“殿下思虑周详,臣仍需仔细推演。”
龙椅上的汉武帝,自始至终沉默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唯有那双深邃的眼睛,在刘据、桑弘羊以及众臣之间缓缓移动,谁也猜不透他心中所想。
直到辩论稍歇,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听不出喜怒:“太子有心了。桑大夫所言,亦是老成谋国之见。盐政之事,关系重大,不可轻率。”
他既没有否定刘据,也没有支持桑弘羊,而是将问题悬置了起来。
“此事,容后再议。”汉武帝挥了挥手,结束了这个话题,“退朝。”
“退朝——”内侍尖细的声音响起。
众臣躬身行礼,依次退出宣室殿。
刘据跟在众人之后,缓缓走出大殿。阳光有些刺眼,他微微眯起了眼睛。后背的朝服,已被冷汗浸湿了一片。
他知道,这场朝会上的交锋,他并没有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自己的能力与价值。但皇帝那句“容后再议”,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依旧高悬于顶。
“盐引”之策,已然摆上了台面。接下来,将是更复杂的幕后博弈,各方势力的角力,以及皇帝最终的权衡。
他抬眼望去,未央宫的天空,依旧湛蓝。但在这片天空下,无形的硝烟,才刚刚开始弥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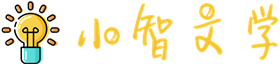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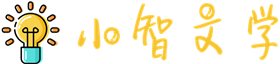 小智文学
小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