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水岸边的靖安侯府,没有寻常勋贵府邸的雕梁画栋。朱漆大门只刷了层清漆,门楣上“靖安侯府”四个字是林缚亲笔写的,笔锋扎实却不张扬;院里的青砖是从关中窑厂调运的旧砖,拼缝处填着细沙,踩上去不滑脚;正屋改作了议事厅,原本的花梨木大桌被换成了十二张榆木方桌,拼在一起能容下二十多人议事——赵宸翊说“议事要敞亮,别搞君臣尊卑那套”,连他自己的位置,也只是在方桌旁多放了把旧木椅。
“殿下,这是今日收到的应聘文书,一共三十七份。”林缚抱着一摞麻纸走进议事厅,纸页边缘有些卷边,是被应聘者反复摩挲过的痕迹,“其中水利相关的十二份,农桑九份,律法五份,还有十一份是杂艺,比如会造水车的木匠、懂种草药的医者。”
赵宸翊正蹲在院里,和鲁大锤一起组装一个曲辕犁模型。听到声音,他直起身,指节因为攥着木榫有些发白——昨夜大理寺传来消息,张狗蛋的尸检报告显示是“吞毒自尽”,可狱卒偷偷透露,死前有个穿锦缎的人去见过他,看服饰像是二皇子府的内侍。“先放桌上吧,”他拍了拍手上的木屑,“挑出几个看着实在的,下午咱们一个个见。”
鲁大锤手里还拿着刨子,木花在他掌心堆成小堆:“殿下,俺看那些应聘水利的,多半是冲着侯府的名头来的,真有本事的老河工,怕是不敢来——二皇子在京里散布谣言,说您这幕僚馆是‘刺探民情的陷阱’,好多人怕被连累。”
赵宸翊没说话,只是拿起模型上的犁评,轻轻转动。这犁评是他按现代机械原理改的,能微调犁铧深度,可要是没人会用、没人会修,再好的东西也只是个摆设。他想起黄河抢险时,王河生凭着几十年经验,一眼就看出堤岸的隐患,那样的人才,才是幕僚馆真正需要的。
“周虎,”赵宸翊突然开口,“你去趟黄河边的王家庄,把王河生老丈请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商,关于黄河汛期后的堤岸维护,还得靠他出主意。”
周虎愣了愣:“殿下,王河生之前说过,不想掺和官场的事,怕得罪人……”
“他不是怕得罪人,是怕咱们办不成事,让百姓失望。”赵宸翊打断他,眼神里带着笃定,“你告诉老丈,我这幕僚馆不搞虚的,就是想找些能做事的人,一起把关中的水利、农桑办好。他要是不来,我就亲自去请。”
周虎应下,转身去备马。林缚看着赵宸翊的背影,突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百姓愿意跟着他——这位侯爷从来不是靠爵位压人,而是靠“实在”,答应百姓的事一定办,需要人才时肯放下身段去请。
下午的应聘面试,设在议事厅旁的小耳房。第一个进来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儒衫,手里攥着一卷《农桑辑要》,手指在书页上抠出了深深的印子。“学生李禾,祖籍华州,家里世代种粮,”年轻人声音有些发颤,却很清晰,“学生读过几年书,也跟着家父种过地,知道关中的土性,也懂怎么选种、怎么防病虫害,想跟着侯爷做事,让百姓多收些粮。”
赵宸翊指了指桌上的粟种——是从西域引来的耐旱品种,颗粒比本地粟种小些,颜色偏黄。“你看看这粟种,在关中的黄土坡上种,该注意什么?”
李禾眼睛一亮,快步走过去,拿起一粒粟种放在手心:“侯爷,这是西域的耐旱粟吧?学生去年在华州见过商队带过!这粟种虽耐旱,可关中的黄土坡地温低,得先把种子用温水泡半个时辰,再拌上草木灰,既能提高发芽率,还能防地下虫。另外,播种时行距得比本地粟种宽两寸,不然通风不好,容易生霉。”
赵宸翊心里一喜。这些细节,是他在西域商队那里听来的,还没来得及整理成册子,李禾竟然知道。“你家里有田吗?今年种了多少?”
“回侯爷,家里有三亩薄田,去年种了半亩西域粟,收成比本地粟多两成。”李禾的腰杆挺得更直了,“只是今年黄河水灾后,田被淹了大半,家父让学生来投奔侯爷,说跟着您,能让更多人种上好粟种。”
“好,你留下。”赵宸翊拿起笔,在李禾的文书上画了个圈,“你负责农桑署,先把西域粟种的播种方法整理成小册子,下周送到关中各村落,教农户们怎么种。”
李禾激动得脸都红了,对着赵宸翊深深一揖:“学生定不负侯爷所托!”
接下来的应聘者,大多是寒门士子或民间匠人,有懂修水渠的,有会造水车的,也有会看地脉的。赵宸翊没问他们读过多少书、有没有功名,只问“实际能做什么”——会修水渠的,就让他画一段渭水支流的修渠图;会造水车的,就让他说怎么解决轮轴磨损的问题;会看地脉的,就让他指认侯府院里哪块地适合打井。
轮到最后一个应聘者时,天已经擦黑了。进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灰布短褂,袖口磨得发亮,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里面是几本账册和一把算盘。“小人宋平,之前在华州县衙做文书,因不肯帮县丞改赈灾粮的账目,被赶了出来。”中年人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硬气,“小人懂律法,也会断些民间纠纷,比如邻里争地、借债还钱的事,侯爷要是不嫌弃,小人想跟着您,为百姓评评理。”
赵宸翊指了指桌上的案卷——是之前华州农户告粮铺掌柜哄抬粮价的案子,案卷里写着“粮价上涨是因漕运受阻,非人为”。“你看看这案子,要是你断,该怎么查?”
宋平拿起案卷,快速翻了几页,手指在“漕运受阻”几个字上停住:“侯爷,这案卷是假的。去年冬天漕运虽冻了半月,可开春后工部已经疏通了河道,粮船早该到了。粮铺掌柜肯定是囤积粮食,故意说漕运受阻,好涨粮价。要查的话,先去码头查粮船到港记录,再去粮铺的后院看有没有囤粮,最后找买粮的农户取证,只要有这三样,就能定他的罪。”
赵宸翊点了点头。宋平说的,和他心里想的一模一样。“你在县衙做了多少年文书?断过多少民间纠纷?”
“回侯爷,做了二十年文书,断过的纠纷有三百多件,没一个百姓说不公的。”宋平从布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这是小人断案的记录,每一件都写了缘由和结果,侯爷可以看看。”
赵宸翊接过小册子,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永宣元年,王家庄王老汉与李老汉争地,查地契是王老汉祖上传下,李老汉因儿子娶媳妇急用钱,想强占,判李老汉归还地亩,并赔王老汉青苗损失费五两”。字迹工整,条理清晰,连王老汉和李老汉的证词都写得明明白白。
“好,你留下。”赵宸翊在宋平的文书上画了圈,“你负责律法署,先去查华州粮铺掌柜哄抬粮价的案子,需要人手或文书,直接跟我说。”
宋平对着赵宸翊躬身行礼,眼眶有些发红:“多谢侯爷信任。小人定不会让侯爷失望,也不会让百姓失望。”
等应聘者都走了,议事厅里只剩下赵宸翊、林缚和鲁大锤。桌上的文书,有二十二份画了圈,大多是寒门士子和民间匠人。“殿下,这么多人,得赶紧把馆署分好,不然会乱。”林缚看着文书,语气里带着兴奋,“咱们可以设水利署、农桑署、律法署、百工署,每个署设一个主管,再配几个帮手,这样分工明确,也方便做事。”
鲁大锤也凑过来:“俺觉得百工署得有个工坊,俺们可以在侯府后院搭个棚子,用来造水车、修农具,还能教农户们怎么用新工具。”
赵宸翊点了点头,拿起笔在纸上画了四个方框,分别写上“水利署”“农桑署”“律法署”“百工署”:“水利署让王河生老丈当主管,他懂黄河和渭水的水性,没人比他更合适;农桑署让李禾当主管,他懂种粮,也了解关中的土性;律法署让宋平当主管,他断案公正,百姓信得过;百工署让鲁师傅当主管,你懂木匠、铁匠的活,能领着大家造工具。”
“俺?”鲁大锤愣了愣,随即挠了挠头,“俺没读过书,怕管不好……”
“管不好的不是你,是那些只会说不会做的。”赵宸翊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只要领着大家把工具造好、把农具修好,就是最大的功劳。要是遇到不懂的,就问林缚,他读过书,能帮你出主意。”
鲁大锤咧嘴一笑:“好!俺听殿下的!俺一定把百工署管好,造最好的工具给百姓用!”
就在这时,周虎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正是王河生。老河工穿着一身蓑衣,裤脚还沾着黄河边的泥浆,脸上的皱纹里嵌着泥沙,却精神矍铄。“侯爷,您找老奴来,是为了黄河堤岸的事?”
赵宸翊连忙迎上去,扶着王河生坐下,给他倒了杯热茶:“老丈,不仅是堤岸的事,我想请您来当水利署的主管,领着大家把关中的水利办好——黄河的堤岸要维护,渭水的支流要疏通,还有各村的水窖要修,这些都得靠您这样有经验的人。”
王河生捧着茶杯,手指在杯沿上摩挲着,没说话。他不是不想来,是怕——二皇子在京里的势力大,要是侯府真的被盯上,不仅自己会遭殃,还会连累跟着做事的人。“侯爷,老奴知道您是为百姓好,可二皇子那边……”
“老丈,我知道您的顾虑。”赵宸翊打断他,语气诚恳,“二皇子是怕咱们把事办好,断了他的财路,才散布谣言吓唬人。可咱们要是因为怕他,就不做事了,受苦的还是百姓。您想想黄河抢险时,那些跟着咱们一起扛沙袋、堵缺口的农户,他们盼着咱们能把水利办好,盼着来年能有好收成,咱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王河生看着赵宸翊,想起黄河决堤时,这位年轻的侯爷和百姓们一起泡在冰冷的水里,一起啃干硬的馒头,一起熬夜堵缺口——这样的官,他这辈子没见过。“好!”老河工突然放下茶杯,声音有些激动,“老奴答应您!就算得罪二皇子,老奴也要跟着您,把关中的水利办好!不让黄河再淹百姓的田,不让渭水再干百姓的地!”
赵宸翊心里一暖,握着王河生的手:“多谢老丈!有您在,我心里踏实多了。”
接下来的几日,靖安侯幕僚馆的馆署很快就建起来了。水利署设在议事厅东侧,墙上挂着关中水利图,桌上堆着测量用的绳尺和木楔子;农桑署在西侧,放着各种粟种、稻种,还有李禾整理的播种小册子;律法署在耳房,宋平带着两个文书,正忙着整理华州粮铺的案卷;百工署在侯府后院,鲁大锤领着几个木匠、铁匠,搭起了工坊,里面放着锯子、刨子、熔炉,还有刚做好的曲辕犁模型。
可麻烦很快就来了。二皇子听说赵宸翊招了不少人才,心里更慌了,派人去应聘者家里捣乱——李禾的父亲在华州种地,被差役以“私种西域粟,不缴赋税”为由,带走关了起来;宋平之前在县衙的同事,被人打了一顿,说是“不该把案卷给宋平看”;王河生的孙子在村里上学,被私塾先生赶了出来,说“家里有人跟着靖安侯,不是良民”。
消息传到侯府时,赵宸翊正在和王河生讨论黄河堤岸的维护方案。老河工听到孙子被赶出来的消息,手都在抖,却强忍着没哭:“侯爷,是老奴连累了家里人……要不,老奴还是走吧,别再给您添麻烦了。”
“老丈,这不是您的错,是二皇子的错!”赵宸翊站起身,眼神里满是愤怒,“他不敢跟咱们明着斗,就只会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周虎,你立刻去华州,把李禾的父亲救出来,再去王河生老丈的村里,给孩子找个新的私塾;林缚,你去县衙,找县令说清楚,就说李禾的父亲是幕僚馆的人,谁敢动他,就是跟我赵宸翊作对!”
周虎和林缚应下,转身就走。王河生看着赵宸翊,眼眶红了:“侯爷,您这么帮老奴,老奴……”
“老丈,咱们是一起做事的,您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赵宸翊扶着他坐下,“二皇子越是捣乱,咱们越要把事办好,让他看看,他吓不倒咱们,也吓不倒百姓。”
没过多久,周虎就回来了,还带来了李禾的父亲和王河生的孙子。李老汉身上还有被差役打的伤痕,却笑着说:“侯爷,谢谢您!那些差役被周护卫教训了一顿,再也不敢找俺麻烦了!俺家的田,俺还种着西域粟,等秋收了,俺一定送些给侯府尝尝!”
王河生的孙子才六岁,扎着小辫子,手里拿着一个木风车,怯生生地看着赵宸翊:“侯爷爷,私塾先生说俺可以回去上学了,还说以后再也不赶俺走了。”
赵宸翊摸了摸孩子的头,心里满是欣慰。他转头对王河生说:“老丈,您看,只要咱们不退缩,二皇子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王河生点了点头,眼神里满是坚定:“侯爷,您放心,老奴一定把水利署管好,不辜负您的信任,也不辜负百姓的期望。”
幕僚馆正式运作的那天,侯府门口挤满了百姓。有的送来了自家种的蔬菜,有的送来了刚烤的馒头,还有的送来了亲手做的布鞋——都是之前黄河抢险时,受过赵宸翊帮助的百姓。“侯爷,您这幕僚馆是为百姓做事的,俺们也没啥好送的,这点东西您收下!”一个老农捧着一筐鸡蛋,非要塞给赵宸翊。
赵宸翊推辞不过,只能收下,又让鲁大锤给每个百姓送了一把新做的小镰刀——是百工署刚造的,刀刃锋利,手柄光滑,正好能用来割麦。“乡亲们,谢谢大家的心意。这镰刀是咱们幕僚馆造的,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年秋收能有好收成。”
百姓们拿着镰刀,都高兴得合不拢嘴。有的当场就试了试,刀刃划过麦秆,“咔嚓”一声就断了,比家里的旧镰刀好用多了。“侯爷,您这镰刀真好!俺们以后种粮、割麦,就更方便了!”
看着百姓们的笑容,赵宸翊心里满是感慨。他知道,幕僚馆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黄河的堤岸要维护,关中的农桑要推广,民间的纠纷要解决,二皇子的阴谋要应对。但他不害怕,因为他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有千千万万支持他的百姓。
可他不知道,此刻的二皇子府里,二皇子正对着亲信大发雷霆。“废物!都是废物!”他把桌上的茶杯摔在地上,碎片溅了一地,“赵宸翊都把幕僚馆开起来了,你们还没找到机会收拾他!本宫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
亲信跪在地上,浑身发抖:“殿下,赵宸翊有百姓支持,还有周虎那样的护卫,咱们根本找不到机会下手……要不,咱们再等等,等他出长安,再在路上动手?”
二皇子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怒火。他知道,现在在长安动手,容易被皇帝发现,只能等赵宸翊出京。“好!就再等几天!”他眼神里满是阴狠,“赵宸翊不是想推广农桑吗?本宫听说,他要去江南考察漕运,到时候,本宫就在江南给他设个陷阱,让他有去无回!”
亲信连忙应下:“殿下英明!只要赵宸翊死了,幕僚馆就散了,关中的百姓也没人管了,储位就是殿下的了!”
二皇子看着窗外的月亮,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赵宸翊,这次本宫看你还怎么逃!
而在靖安侯府里,赵宸翊正和幕僚馆的众人一起,在院里吃晚饭。桌上摆着百姓送的蔬菜和馒头,还有鲁大锤炖的肉汤,虽然简单,却吃得热闹。李禾在说农桑署的计划,要在关中推广西域粟种;宋平在说律法署的进展,华州粮铺掌柜的案子快查清了;王河生在说水利署的安排,要去渭水支流查淤堵情况;鲁大锤在说百工署的新想法,要造一种能灌溉的水车,不用人力推,靠水力就能转。
赵宸翊看着大家,心里满是希望。他举起碗,对着众人说:“各位,咱们幕僚馆能有今天,靠的是大家的信任,靠的是百姓的支持。接下来,咱们一起努力,把水利办好,把农桑办好,把律法办好,让关中的百姓能安居乐业,让大雍的江山能更稳固!我先干为敬!”
众人也举起碗,齐声说:“愿随侯爷,为百姓做事!”
碗与碗碰撞的声音,在院里回荡,和远处渭水的流水声、百姓的笑声,混在一起,成了长安城里最温暖的声音。可赵宸翊知道,这温暖的背后,还有二皇子的阴狠和算计。他放下碗,看向江南的方向,眼神变得坚定——不管二皇子在江南设了什么陷阱,他都要去,不仅要考察漕运,还要查清漕运的积弊,为百姓解决漕粮运输的难题。
一场新的挑战,正在江南等着他。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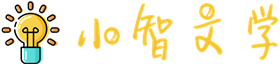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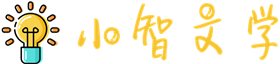 小智文学
小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