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棠挎着空竹篮转过村口老槐树时,日头正往西山坠,晚霞把青石板路染得像撒了层金箔。
周梅早等在院门口,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踮着脚往路上望,见着人影就蹦起来:”阿姐!
阿姐!”
“梅儿。”沈棠蹲下身,把周明买的糖霜饼从怀里掏出来。
糖霜沾着她粗布衣襟的褶皱,周梅却像见着珍宝似的捧住,鼻尖几乎要贴上去:”好香!”转头又往周明怀里钻,”阿兄买的?”
周明耳尖又红了,别过脸去咳了声:”阿姐给的钱。”
沈棠站起身,看见周承安已经把竹筐卸在院角。
他正弯腰解麻绳,后背的补丁被夕阳拉得老长。
她摸了摸怀里的布包,银钱隔着粗布硌得肚皮发暖——这是她头回攥着这么实在的家当。
“阿姐看!”周梅突然拽她的袖子,举着糖霜饼往她嘴边送,”甜的!”
沈棠咬了一小口,糖渣落进脖颈里,痒丝丝的。
她望着院里那口缺了沿的陶缸,缸里泡着新摘的嫩姜——明儿再腌两坛,赶早集还能多卖些。
可想起老井边那两个农妇的话,她又皱起眉:”承安,你明儿去河坝看看?
今春雨水多,坝子要是塌了,咱们那三亩荒田首当其冲。”
周承安直起腰,手掌蹭了蹭裤腿上的泥:”我夜里就去。”他说话总像石头砸进井里,闷声闷气的,可沈棠知道,他应下的事准保落得实。
灶房里飘出红薯粥的甜香时,院外传来”笃笃”的敲门声。
周明去开门,回来时身后跟着个穿粗布短打的老汉——是村东头的张大伯,脸上的皱纹里还沾着草屑,手里提着半袋新收的麦种。
“大妹子。”张大伯把麦种往石桌上一放,笑得眼角堆起褶子,”我家那混小子说,你们在村南头垦荒田?”
沈棠忙搬了条长凳:”伯您坐。
是想着多开点地,总比守着那两亩薄田强。”
“好!”张大伯拍了下大腿,震得石桌都晃了晃,”我就瞧着你们小两口有奔头!
昨儿我给牛喂草,听王二家的说你在集上卖腌菜,把李婶子那嘴硬的都镇住了——”他忽然压低声音,”那李婶子早年嫌我家穷,说我闺女嫁不出去,今儿我可算扬眉吐气回!”
周承安从灶房端出碗茶,放在张大伯手边。
沈棠见他耳尖微微动了动,知道他在憋笑——这木讷汉子,偏生爱听这些解气的事。
“我来是说正事儿。”张大伯喝了口茶,”明儿我叫上老李家的小子、东头的栓子,咱们带犁耙去帮你们垦荒。
那地荒了五六年,草根子扎得深,你们小两口带着俩娃,哪吃得消?”
沈棠手一抖,茶碗差点没拿稳。
她望着张大伯鬓角的白发,想起上个月他摔了腿,还是她送的跌打药。
原来这老头记着呢——她喉头突然发紧:”伯,这怎么好意思…”
“有啥不好意思?”张大伯把茶碗一推,”当年我盖房缺梁木,是你家公爹砍了后山那棵老槐给我;前儿你给我送药,还往药包里塞了俩鸡蛋。
咱们庄户人,不就图个帮衬?”
周明蹲在门槛边剥蒜,突然插了句:”张大伯,我阿爹…周老爹?”
“你阿爹是好人。”张大伯拍了拍周明的肩,”他走那年,我蹲在你家院门口哭了半宿。”
灶房里传来”当啷”一声,是周承安碰翻了菜勺。
沈棠转头看他,见他背对着众人,肩膀微微起伏——她知道,他又想起那个雪夜了。
周父咽气前攥着他的手,说”承安,这媳妇你得护着”,他应了,就真把这辈子的热乎气都给了她。
“就这么定了!”张大伯站起身,拍了拍裤腿的麦麸,”明儿辰时我带人来。
大妹子,你让娃多蒸点馍,咱们干起活来,可都是虎狼胃!”
他跨出院门时,晚霞正漫过他的后背,把影子拉得老长,像道护着小院的墙。
第二日天刚放亮,沈棠就被院外的说话声惊醒。
她掀开粗布帘子,见张大伯带着四个壮实后生站在门口,手里的犁耙、铁锨在晨露里闪着光。
栓子扛着把大镐,冲她咧嘴笑:”大嫂子,咱今儿准保把那三亩地翻得比新媳妇的脸还光溜!”
周承安已经套好了牛车,车斗里堆着半袋盐——沈棠昨儿特意去集上买的,干活的人出汗多,得补盐。
周明抱着个瓦罐跑出来,里面是新腌的酸黄瓜:”阿姐说,晌午配馍吃!”
荒田在村南头,野草长得比人高。
张大伯抡起犁耙往地上一插:”都听我指挥!
栓子带俩小子割草,老李家的跟我犁地,承安你把草根子拾掇干净!”
日头爬到头顶时,地里的荒草早堆成了小山。
沈棠提着瓦罐来回跑,给每人递水送黄瓜。
栓子啃着酸黄瓜直咋舌:”大嫂子,你这腌菜比我娘的手艺还绝!
明儿我让我媳妇来跟你学!”
“学啥?”老李家的抹了把汗,”大嫂子这是吃饭的本事,哪能随便教?”
沈棠笑着往他瓦罐里添水:”都是乡里乡亲的,有啥不能教?
等我腌菜坊支起来,还得请婶子们来帮忙呢。”
众人哄笑起来,犁耙声、谈笑声混在一起,惊得田边的麻雀扑棱棱飞上天。
周梅蹲在田埂上,用树枝在泥里画小房子,画着画着就唱起来:”荒田变金窝,阿姐最能干…”
周明本来在拾草根,听见妹妹的歌,耳尖又红了,却没像往常那样呵斥,反而从怀里掏出块糖霜饼,掰了一半塞给周梅。
日头偏西时,三亩荒田终于翻得平平整整。
张大伯蹲在田边,用指节敲了敲新翻的土:”这地养了几年,肥着呢。
明儿撒上麦种,等开春准保能收两石!”
沈棠蹲下身,捧起一把泥土。
湿软的土粒从指缝漏下去,带着太阳的温度。
她想起刚分家那会儿,这地还是一片荒草,她蹲在草窠里哭,周承安悄悄把外套披在她肩上,说”有我呢”。
现在,泥土里混着十多个人的汗味,混着希望的味道。
“大妹子。”张大伯递来烟袋,”你记着,咱村的人不欺生,谁要是真心过日子,咱们就捧谁。”他吸了口烟,烟圈飘向远处的河坝,”就是那周家族里的…你可得防着点。
前儿我见周老三在酒坊喝酒,说要找你要’族田管理费’。”
沈棠的手顿了顿。
她望着河坝方向,那里的柳树被风吹得摇晃,像谁在暗中招手。
周老三是周父的堂弟,分家时闹得最凶,说”童养媳也配当主母”,还砸了她半坛腌菜。
“我知道。”她把泥土攥紧,指缝里渗出湿印子,”但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傍晚回家时,夕阳把荒田染成了金色。
周梅骑在周明脖子上,唱着跑在前头。
周承安扛着犁耙,走在最后,影子和沈棠的影子叠在一起。
“明儿我去集上。”沈棠摸了摸怀里的布包,里面还剩二两银子,”买些麦种,再看看有没有便宜的陶瓮——腌菜卖得快,得备足坛子。”
周承安嗯了声,突然伸手把她鬓角的草屑摘下来:”我陪你去。”
沈棠抬头看他,他耳尖有点红,却直直望着她的眼睛。
她突然笑了,把布包往他手里一塞:”成,你帮我看秤,省得那些奸商坑我。”
夜里,沈棠在灶房擦陶瓮。
月光从破窗棂漏进来,照在她沾着盐渍的手背上。
她数着坛子里的腌萝卜,想着明儿要带哪几坛——糖蒜最抢手,得留两坛;酱黄瓜脆,给王嫂子留一坛;还有那坛加了蜜枣的萝卜,得留给李婶子…
院外传来风吹竹帘的声响,她抬头望了眼。
墙角的老母鸡已经睡了,周承安的蓑衣挂在桃树上,被月光照得发白。
明天又是个好天。
她想着,把最后一坛腌菜封好,泥封上还留着她的指印,像朵小小的花。
晨雾还未散透,沈棠就着灶膛里的余火煮了碗热粥。
粗陶碗沿沾着米粒,她用袖口擦了擦,端到院中的石桌前。
周承安已经把竹筐绑上扁担,竹筐里码着六坛腌菜,最上面盖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边角还绣着朵歪歪扭扭的喇叭花——是周梅昨晚偷偷缝的。
“先喝口粥。”她把碗推过去,自己蹲在筐边检查泥封。
最左边那坛糖蒜的泥封有点松,她用手指蘸了点水,轻轻按实:”昨儿后半夜听见下雨,得再紧一紧,别让水汽渗进去。”
周承安捧着碗,看她发顶沾着的灶灰,伸手想拍,又怕碰乱了她梳的髻。
最终只是把自己的粗布汗巾递过去:”擦把脸,露水重。”
沈棠接过来擦了擦额头,指尖触到汗巾上洗不掉的草汁味——这是他每次上山打柴都要带的。
她忽然想起分家那年冬天,自己蹲在草棚外哭,他也是这样把汗巾递给她,说”哭完了就吃饭,饿着肚子没法翻地”。
“明儿开始要往镇里供货了。”她把最后一坛酱黄瓜摆正,”张掌柜说每月要二十坛,我得让明儿去河边割芦苇,编些草垫衬坛底,路上颠不碎。”
周承安喝了口粥,喉结动了动:”我夜里去砍了竹子,明儿劈成竹片,给筐子加层底。”他低头扒拉米粒,声音闷在碗里,”你说要多雇俩帮工,我问过大伯家小子,他愿意来,一天给两文钱就行。”
沈棠抬头看他,晨光里他眼角的细纹被照得清楚。
这个从前只会扛着猎枪闷头走的男人,现在会偷偷记她的话,会在半夜磨竹子,会把所有打算都藏在粥碗里。
她鼻子一酸,低头用指甲在泥封上按了朵小花:”等赚了钱,给你做身新衣裳,蓝布的,像上次集上看见的那样。”
周承安的耳朵瞬间红到脖子根,端碗的手一抖,粥洒在青布裤上。
他手忙脚乱去擦,沈棠笑出了声,把竹筐的提手往自己肩上送:”我挑前半程,你挑后半程,省得压坏了腌菜。”
集市的青石板还沾着露水,沈棠的粗布鞋踩上去发出”吱呀”声。
她熟门熟路地走到西头老柳树下——这是她卖了三个月腌菜的老位置,树洞里还塞着她藏的半块砖,用来压摊位布。
“哟,沈家嫂子今儿来得早!”卖豆腐的王大叔掀开木盖,舀了碗豆浆递过来,”给孩子带的?
我多放了糖。”
沈棠接过来,从筐里摸出个小陶瓶:”上回您说爱吃辣萝卜,这坛我特意多搁了红辣椒。”王大叔眼睛一亮,把豆浆往她手里塞得更紧:”得嘞,您这腌菜往这儿一摆,我这豆腐都能多卖两板!”
她刚揭开盖菜的蓝布,腌菜的香气就裹着甜、酸、鲜往人鼻子里钻。
隔壁卖针线的林氏凑过来看,用针挑了块糖蒜:”哟,这蒜白得像玉,咬着嘎嘣脆!”她咬了一口,眼睛立刻弯成月牙,”给我留两坛,我那口子就好这口!”
“婶子您尝尝这个酱黄瓜。”沈棠笑着递过竹夹子,”我用新收的嫩黄瓜,晒了半干再腌的,脆得能听见响。”林氏嚼着黄瓜,顺手把针线筐往旁边挪了挪:”您摆这儿,我给您看着摊子,保准没人摸坛子!”
日头升到树顶时,筐里的坛子已经空了三个。
沈棠正低头算钱,肩头被人轻轻碰了碰。
她抬头,就见穿月白湖绸衫的张掌柜站在面前,手里捏着块从林氏那儿讨来的糖蒜。
“沈姑娘的腌菜,果然名不虚传。”张掌柜把糖蒜嚼得脆响,”上回我那内宅的姨太太尝了您的蜜枣萝卜,直夸比城里醉仙楼的还地道。”他指节敲了敲剩下的坛子,”我那铺子在镇东头,每日往来的商客多。
您若愿意把腌菜供到我那儿,每月要多少坛随您开价。”
沈棠的手指在围裙上蹭了蹭——这是她紧张时的习惯。
她想起昨晚在灶房算的账:现在家里有五口大陶瓮,每日能腌三坛,除去自己吃和集市卖的,每月能匀出十五坛。
但张掌柜要的是长期,得留有余地。
“每月二十坛,成吗?”她抬头,目光清亮,”您给的价得比集市上每坛多五文——我得雇人帮忙腌,还得置新瓮。”
张掌柜抚着八字胡笑了:”沈姑娘好算计。
行,就二十坛,每坛比集市多八文。”他从怀里摸出个铜锁小匣子,”这是定金,先给您五钱银子。
等下月初我派伙计来拉第一车,您看……”
“成!”沈棠还没说完,身后突然响起尖嗓子。
李婶子扒开围观的人,手里举着根腌萝卜:”我当是多金贵的东西,敢情就是坛咸菜!
昨儿我家那口子还说,周家的童养媳就会偷学老主家的手艺,上不得台面——”
她的话被自己咬萝卜的声音打断。
原本绷着的脸突然松了,眼睛瞪得溜圆,腮帮子鼓得像青蛙:”这……这萝卜咋带蜜味儿?”
“李婶子好眼力。”沈棠把算盘推到桌角,”这是我用前儿集上买的蜜枣腌的,枣核都泡软了,您尝尝看。”她又夹了块糖蒜递过去,”这蒜是用新晒的红糖渍的,不齁嗓子,您家小孙子肯定爱吃。”
李婶子咬着糖蒜,嘴还硬:”谁…谁要给那小崽子带?
我就是…就是尝尝你有没有偷工减料!”她伸手去摸钱袋,又猛地缩回来,”我就买半坛!
省得吃不完坏了!”
“成。”沈棠笑着给她装坛,”半坛三一文,我给您抹个零,三十文。”她把坛子往李婶子怀里送,”您拿好喽,这泥封可金贵,回去要是放阴凉地儿,能存三个月呢。”
李婶子抱着坛子挤出去时,撞翻了林氏的针线筐。
沈棠蹲下去帮着捡针,听见她跟隔壁卖菜的赵婶子嘀咕:”就那蜜枣萝卜,比我家过年煮的甜汤还香……”
日头偏西时,筐里只剩个空坛子。
周承安从镇外回来,肩上多了捆新竹片——他说要给筐子加固。
沈棠把钱袋递给他,里面的铜板撞得叮当响:”张掌柜给的定金,你收着。
明儿咱们去买麦种,再捎两坛腌菜给张大伯,谢他帮着翻地。”
周承安接过钱袋,往她手里塞了个油纸包:”我路过茶摊,见那卖桂花糕的,你昨儿说想吃……”
沈棠打开纸包,桂花香混着糖香扑出来。
她掰了半块塞他嘴里,自己咬了半块。
甜丝丝的味道漫开时,她看见周梅和周明从街角跑过来,周明手里举着根糖葫芦,周梅的辫梢沾着草屑——准是又去河边掏鸟窝了。
“娘!”周梅扑进她怀里,糖葫芦上的红果蹭了她一身,”张大伯说咱家的腌菜能卖去镇里,他明儿要帮咱们挖新菜窖!”
沈棠摸着她的小辫,抬头看向远处。
镇外的荒田已经翻出黑油油的土,几个村民正扛着锄头往回走,看见她都笑着招手。
风里飘来新翻泥土的腥甜,混着腌菜的酸香,混着桂花糕的甜,混着周承安身上淡淡的松木香。
她忽然想起分家那天,自己蹲在荒草里哭,周承安把外套披在她肩上说”有我呢”。
现在她有周承安,有明儿梅儿,有张大伯,有王大叔,有整个愿意捧她的村子。
那些说”童养媳当不了主母”的周老三们,那些躲在柳树后说风凉话的,终会被这混着希望的风,吹得远远的。
“走,回家。”她牵起两个孩子的手,周承安扛起空筐走在后面。
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叠在一起,像株扎根很深的树。
李婶子抱着半坛腌菜从巷口转出来,望着那串渐渐走远的影子,又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坛子。
泥封上有朵小小的指印,在夕阳里闪着光,像朵开得正好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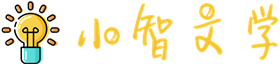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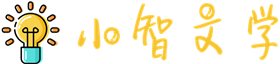 小智文学
小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