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的望溪还浸在浓淡不一的雾里,林砚推着摩托车走在山路上,裤脚蹭过带露的野草,湿凉的水汽顺着布料往上钻。山路是村民踩出来的土路,雨后坑洼里积着水,摩托车轮碾过去,溅起的水花打在路边的野菊上,黄灿灿的花瓣颤了颤,把香气混着雾气送过来。
他在陈冬家的土坯房外停住时,烟囱刚冒起青灰色的烟,烟柱被风扯得歪歪的,绕着房檐转了两圈才散开。院门没锁,是用两根旧木杆搭着的简易门,林砚轻轻一推,门轴就发出“吱呀”的声响。院里堆着半垛干柴,柴垛旁的石磨上,放着个豁口的搪瓷盆,盆里泡着要洗的旧衣服,水色发浑,浮着几点洗衣皂的泡沫。
“林老师?”屋里传来老人的声音,带着晨起的沙哑。林砚抬脚进门,就见陈冬蹲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后背绷得笔直,正用根磨得光滑的柴棍拨灶膛里的火。火光照在他脸上,映得两颊泛着红,鼻尖沾了点黑灰,像只刚偷尝过灶糖的小猫。他身旁的矮凳上,陈冬的舅公正坐着,左手攥着根粗针,右手捏着段蓝布,正往陈冬磨破的校服袖口上缝——老人的右手风湿犯了,指关节肿得像小馒头,捏针时指尖抖得厉害,线脚歪歪扭扭,却缝得格外紧实,每一针都扎得很深。
“大爷,您怎么又自己缝衣服?”林砚走过去,轻轻按住老人的手。舅公抬头笑时,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冬冬这衣服袖口磨得没法穿了,他正是长身子的时候,总不能让他露着胳膊上学。”陈冬听见这话,拨火的动作顿了顿,把柴棍往灶膛里再送了送,火舌“腾”地窜起来,把他的影子映在土墙上,忽高忽低。“我不冷,舅公。”他小声说,小手被烟火熏得发红,却还是把灶膛边烤得温热的红薯往舅公脚边推了推,“等会儿吃热的。”
林砚没接话,转身走到摩托车旁,把绑在后座的小凳子解下来。凳子是他从镇上旧货市场淘的,凳面磨得发亮,他怕陈冬坐得硌,特意从自己的旧毛衣上拆了块绒布垫在上面,用棉线缝了两道,布边虽毛糙,却软乎乎的。“上来吧,再晚要赶不上早读了。”他扶着凳子喊陈冬。
陈冬攥着衣角犹豫了两秒,校服下摆被他攥出几道褶子。以前林砚送他上学,他总坐得离林砚远远的,手也只敢轻轻搭着车座边,今天却往前挪了挪,小屁股稳稳地坐在绒布上,小手悄悄抓住了林砚的衣角——不是松松垮垮地搭着,是指尖微微用力,把布料攥出了个小团。
摩托车驶离院子时,舅公还站在门口喊:“林老师,路上慢点!”陈冬回头望了一眼,见老人还扶着门框站着,赶紧把头转回来,贴在林砚的后背。风从耳边吹过,带着野菊的香和泥土的腥气,他忽然把脸埋在林砚的外套上,声音闷乎乎的:“林老师,我想给爸爸打电话,可舅公记不清号码了。”
林砚的后背能感觉到孩子温热的呼吸,心里猛地一酸。他想起上周三的下午,自己放了学就往镇上跑,托开小卖部的张婶打听——张婶的儿子在县城工地上干活,说不定能问到陈冬爸爸的消息。张婶帮着打了三个工地的电话,才在城郊的一个建材厂里找到人,电话那头的工头说,陈冬爸爸在那儿搬钢筋,白天手机都关着,只有晚上下工了才开机。
周五下午放学,林砚把陈冬叫到办公室。办公室是间小土房,墙皮掉了好几块,靠窗摆着张旧办公桌,桌上放着部带天线的座机,是教学点唯一的通讯工具。林砚拨电话时,指尖都有点发紧,陈冬就站在桌旁,小手背在身后,盯着电话机上的按键看,脚尖在地上蹭来蹭去,把水泥地蹭出一道浅痕。
“嘟——嘟——”电话响了三声,那头终于接了,先是一阵嘈杂的机器声,接着传来沙哑的男声:“喂?谁啊?”
陈冬的身子猛地绷紧,像被冻住了似的,肩膀微微耸着,好半天才抬起手,轻轻攥住了听筒。他把听筒贴在耳朵上,嘴唇动了好几下,才憋出一声“爸爸”,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刚说完,眼泪就砸了下来,落在摊在桌上的作业本上,晕开一小片湿痕——那是他当天的生字作业,最上面写着个“家”字,宝盖头歪歪扭扭,下面的“豕”却一笔没少,像是生怕漏了什么。
“冬冬?”听筒里的声音顿了顿,机器声似乎小了些,“你怎么打电话来了?舅公身体还好吗?”
陈冬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哭,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家”字的笔画上,把“豕”的最后一笔晕成了个小小的墨点。林砚怕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悄悄拍了拍他的后背,递过一张皱巴巴的纸巾。陈冬接过纸巾,却没擦眼泪,只是攥在手里,把听筒往耳边再贴了贴,哽咽着说:“舅公……舅公风湿犯了,我帮他拨火、喂饭……”
“乖孩子,”那头的声音软了些,带着点愧疚,“爸爸再干两个月,等过年就回去,到时候带你去镇上买新书包,买你最想要的铅笔盒。”
“真的吗?”陈冬猛地抬头,眼泪还挂在睫毛上,眼睛却亮了,像落了星光。他攥着作业本的手忽然松开,指尖轻轻碰了碰晕开的墨点,像是在确认什么,“爸爸,我今天写作业没缺页,林老师还夸我‘家’字写得好……”
电话那头又说了些什么,林砚没太听清,只看见陈冬不停地点头,偶尔应一声“嗯”“知道了”,嘴角慢慢翘起来,连眼泪都忘了擦。挂电话时,他攥着听筒不肯松手,手指摩挲着听筒上磨得发亮的塑料壳,直到林砚催他“该写作业了”,才慢吞吞地把听筒放回去,转身从书包里掏本子时,脚步都比平时轻快了些。
那天的作业确实不一样。以前陈冬总用铅笔写作业,写得不好就用橡皮擦掉,纸页上满是擦痕,偶尔还会缺页——不是弄丢了,是他觉得写得差,偷偷撕了藏起来。可那天他用的是舅公给他的红钢笔,笔帽上缠了圈胶布防漏墨,字迹虽还不算工整,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整本作业都写得满满当当,连页脚的空白处,都画了个小小的太阳,和林砚在他作文本上画的一模一样。
“林老师,”陈冬把作业本递过来时,声音还带着哭腔,却比平时亮了些,他仰着头看林砚,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的小兔子,“我爸爸说,等过年就回来,带我去买新书包。”
林砚摸了摸他的头,指尖蹭过他额前的碎发,忽然注意到他校服袖口磨破的边里,露出一截冻得发红的手腕,连指关节都泛着青。他心里一动,转身拉开办公桌的抽屉——里面放着副灰色的旧手套,是他上大学时买的,掌心有防滑的胶粒,只是手腕处有点松。他把手套拿出来,递给陈冬:“戴上吧,别冻着了。”
陈冬接过手套,愣了愣才往手上套。手套确实大了些,他的小手钻进手套里,指尖露不出来,手腕处还空荡荡的,一甩就往下掉。林砚看着好笑,又有点心疼,从抽屉深处翻出个针线盒——那是李老师送他的,里面的线颜色不全,却还能用。他挑了段和手套颜色相近的灰线,让陈冬把手套递过来:“我给你缝两圈松紧带,就不会掉了。”
陈冬乖乖地把手套放在桌上,站在旁边看林砚缝。林砚的手指不算灵巧,穿针时试了三次才把线穿进去,缝的时候没留神,针尖戳在了指腹上,冒出个小小的血珠。“老师!”陈冬赶紧凑过来,伸手想碰他的手指,又怕碰疼了,只敢轻轻吹了吹,“您小心点。”
林砚笑着摇头,继续缝。他在手套手腕处缝了两圈松松的线,拽了拽,刚好能卡住陈冬的小臂,不会太紧,也不会掉。“试试?”他把缝好的手套递给陈冬。陈冬赶紧套上,活动了下手指,虽然还是有点大,却稳稳地贴在手上,不会再往下滑了。他攥了攥拳头,又松开,反复试了好几次,嘴角的笑越来越明显,最后干脆把手套举起来,对着窗外的阳光看,像是在欣赏什么稀世珍宝。
那天傍晚送陈冬回家,摩托车后座的小凳子上,多了一束野菊。是陈冬在路边摘的,黄灿灿的一大束,花茎上的刺都被他仔细掐掉了,还用草叶缠成了束,怕扎到林砚的手。他把花插在林砚的车把上,小声说:“林老师,这花好看,你插在办公室里。”
摩托车驶在山路上,野菊在车把上晃来晃去,花瓣上的露珠顺着车把往下滴,落在林砚的手背上,凉丝丝的,却让他心里暖得发烫。陈冬坐在后面,小手还是抓着他的衣角,忽然说:“林老师,你上次说春天种向日葵,咱们能种在操场的排水沟旁边吗?我爸爸说,向日葵跟着太阳转,等它开花了,爸爸说不定就回来了。”
“当然能。”林砚回头笑了笑,看见陈冬的脸上映着夕阳的光,眼睛亮得像藏了小太阳,“到时候咱们一起种,你负责浇水,我负责翻土,等花开了,咱们就拍照片,寄给你爸爸看。”
陈冬用力点头,把脸贴在林砚的后背,声音里满是期待:“好!”
从那天起,陈冬像是换了个人。以前他在教室里总缩在座位上,课间也躲在角落,别人喊他玩,他要么摇头,要么小声说“不了”;现在他会主动帮同学捡掉在地上的文具,有人忘带橡皮,他还会把自己的橡皮掰成两半递过去。上周二的美术课,李老师让大家画“最想做的事”,陈冬画了幅画:画面中间是个大大的向日葵,花盘里站着三个小人,一个戴眼镜(是林砚),一个拄着拐杖(是舅公),还有一个高高瘦瘦的(是他爸爸),三个小人手拉手,旁边写着歪歪扭扭的五个字:“一起种向日葵”。
李老师把画拿给林砚看时,林砚正坐在办公室里改作业。他看着画上的小人,忽然看见画的右下角,有个小小的粉笔头图案——和他笔筒里那两截粉笔一模一样。他想起那天陈冬塞给他粉笔头时说的话:“老师,这个你留着画板书,比新粉笔好握。”
课间的时候,林砚把陈冬叫到办公室,指着画上的向日葵笑:“画得真好看,等春天种的时候,咱们就按你画的来,种一大片向日葵。”
陈冬站在桌旁,手还戴着那副缝了松紧带的手套,听见这话,嘴角抿出个浅浅的笑,比画里的向日葵还好看。他抬头看林砚,忽然说:“林老师,我昨天给爸爸写信了,舅公帮我念,我写的,信里说你帮我缝手套,还说咱们要种向日葵。”
“那你爸爸肯定会很高兴。”林砚摸了摸他的头,忽然看见他校服袖口的蓝布补丁——是舅公缝的,虽然不好看,却很结实。他想起清晨老人缝衣服时颤抖的手,想起陈冬拨火时发红的小手,想起电话里那声沙哑的“乖孩子”,忽然觉得,有些转变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藏在柴棍拨火的声响里,藏在缝补校服的线脚里,藏在野菊的香气和向日葵的期待里。
那天晚上,林砚回到自己的小房时,车把上的野菊还没蔫。他找了个空玻璃瓶,灌了点水,把野菊插进去,放在书桌的窗台上。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落在花瓣上,泛着淡淡的光。他翻开教案本,在空白页上写下:
“今天批改作业时,看见陈冬的作业本上画了向日葵。他以前总把写得不好的作业撕掉,现在却愿意把心事画在上面;以前连说话都不敢抬头,现在会主动说要给爸爸写信。原来真正的教育,不是推着孩子往前走,而是给他们一点光——一点来自电话那头的期盼,一点藏在手套里的温暖,一点关于向日葵的约定,他们就能顺着光,慢慢长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写完,他抬头看了眼窗台上的野菊,忽然发现花茎下压着张小小的纸条,是陈冬偷偷塞进去的。纸条上画着个小太阳,旁边写着:“林老师,谢谢你。”字迹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写得格外认真。
林砚把纸条夹进教案本里,和陈冬的作文本放在一起。窗外的月光更亮了,照在教学点的操场上,仿佛能看见春天的样子——排水沟旁边种满了向日葵,花盘朝着太阳,陈冬蹲在花田里,手里拿着水壶浇水,旁边站着林砚,还有个高高瘦瘦的男人,正笑着摸陈冬的头。
他知道,等春天来的时候,这幅画一定会变成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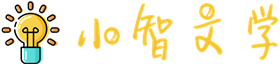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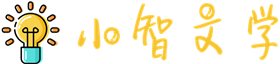 小智文学
小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