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约市,自由双塔轰然倒塌的烟尘还未散尽,花旗国克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空气就已凝固成冰冷的铁。
大统帅的拳头砸在桌面上,咖啡杯里的液体溅出,在标着“绝密”的文件上晕开深色的痕迹,如同那场灾难中无法抹去的血迹。
当天下午,花旗国司法部就像射出一支带着火焰的箭,将亚太山地班国的登高一钉在了“全球头号通缉犯”的榜单顶端——悬赏金额从最初的2500万美元一路飙升,最后像座沉甸甸的金山,悬在全世界每一个情报贩子的头顶。
可这座金山,却在接下来的九年里,成了花旗国手中最烫手的烙铁。
登高一像一缕藏在风里的烟,没人知道他究竟躲在班国哪片山地的山洞里。
花旗中情局的特工们,像疯了一样在班国的崇山峻岭中搜寻,他们翻遍了每一个能藏人的岩缝,盘问了每一个可能知情的牧民,甚至把卫星镜头对准了班国西部最偏僻的雪山,可拍到的永远只是随风飘动的经幡,或是在山谷里啃草的山羊。
有一次,特工们得到线报,说登高一藏在兴都库什山脉深处的一个山洞里,他们立刻调动了三架“捕食者”无人机,对着山洞所在的山头狂轰滥炸,把整座山炸得像个满是疮疤的烂土豆。
可等地面部队冲上去一看,山洞里只有几只受惊的旱獭,还有一堆早已冷却的篝火灰烬——登高一早就像泥鳅一样,从他们的包围圈里溜了。
花旗联军的士兵们,更是被这场无休止的搜寻折磨得快要崩溃。
他们背着几十斤重的装备,在班国的山路上日复一日地巡逻,脚下的碎石子磨破了他们的军靴,山顶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他们的脸上。有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士兵,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就像在跟一个幽灵打仗,我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甚至不知道自己每天走的路,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时候,他们会在山洞里发现一些登高一留下的痕迹——一件沾着泥土的阿拉伯长袍,一本写满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或是一个用来烧水的铜壶。
可这些痕迹,就像故意留下的诱饵,等他们顺着线索追下去,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反美武装的伏击。
有一次,一支巡逻队跟着一串脚印走进了一条峡谷,结果峡谷两侧的山坡上突然冒出密密麻麻的枪口,子弹像下雨一样打下来,最后只有两个士兵活着逃了出来,他们的防弹衣上,被子弹打穿的孔洞像筛子一样密集。
花旗中情局为了找到登高一,几乎把整个山地班国的情报网络都翻了个底朝天。
他们收买了山地班国的各部落长老,策反了反美武装的底层士兵,甚至把特工伪装成商人,在山地班国的集市上和人套近乎。
可登高一的保密工作,做得比铁桶还严实。
他身边的人,都是跟着他打了十几年仗的死忠,就算被抓住,也宁愿咬碎嘴里的毒药,也不肯吐露半个字。
有一次,中情局抓住了一个据说给登高一送过信的信使,他们把他关在坎大哈的秘密监狱里,用了各种手段审讯,可这个信使就像块捂不热的石头,除了重复“我什么都不知道”,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
最后,中情局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监狱里绝食而死,连一点有用的情报都没捞到。
时间一天天过去,花旗国国内的不满声越来越大。
媒体们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批评政府“无能”,民众们举着“还我亲人”的标语在白宫前抗议,甚至有议员在国会山上拍着桌子,要求总统给个说法——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死了这么多士兵,连一个登高一都抓不到?大统帅的压力越来越大,他把中情局局长叫到办公室,拍着桌子骂道:“如果再找不到登高一,你就卷铺盖滚蛋!”中情局局长吓得满头大汗,回到局里后,立刻把所有特工都派了出去,甚至不惜越过山地班国边境,把情报网延伸到了隔壁的老印、巴铁等国。
转机,终于在2010年的夏天出现了。
一个潜伏在巴铁国首都伊斯兰堡的中情局特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从一个巴铁国官员的嘴里听到了一个名字——“阿伯塔巴德”。
那个官员说,在阿伯塔巴德的郊区,有一座奇怪的 compound(院落),院子的围墙高达三米,上面还拉着铁丝网,院子里的人从不和邻居来往,甚至连垃圾都要自己烧掉,像是在隐藏什么秘密。
这个消息,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中情局特工的神经——他立刻把这个消息传了回去,中情局总部的分析师们,像是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立刻开始对这座院落展开调查。
他们调出了阿伯塔巴德的卫星地图,发现这座院落果然像个孤立的堡垒,坐落在一片居民区中间,却和周围的房子格格不入。
院子里有三栋楼,其中一栋三层小楼特别显眼,窗户很少,而且都装着厚厚的窗帘,就算是白天,也看不到里面的人影。
分析师们盯着卫星图像,看了一天一夜,他们发现,这座院子里的人,从来不在外面活动,只有几个穿着传统长袍的女人,会偶尔隔着围墙,和外面的小贩买点东西。
更可疑的是,院子里经常有一个高个子男人,在二楼的露台上散步,他的身形和走路姿势,和登高一的档案照片惊人地相似——只是因为卫星图像不够清晰,他们不敢确定。
为了摸清院子里的情况,中情局派了一个特工,伪装成一个卖冰淇淋的小贩,在院子附近摆摊。
那个特工每天推着冰淇淋车,在院子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卖冰淇淋,一边偷偷观察院子里的动静。
他发现,院子里的守卫特别严密,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有一个男人拿着枪,在围墙上面巡逻。
有一次,一个小孩不小心把球踢到了院子的围墙上,立刻有两个男人从院子里冲出来,把小孩吓得哇哇大哭,还警告周围的邻居,不许靠近院子半步。
这个特工把看到的一切都记在心里,他越观察,越觉得这座院子里藏着不简单的人物——这里的戒备,比巴铁国的军事基地还要森严。
中情局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了更多关于这座院子的情报。
他们通过监听附近的电话线路,发现这座院子里从来没有接通过固定电话,也没有人使用过手机——这在现代社会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们还发现,这座院子的水和电,都是通过地下管道和线路供应的,和周围的居民区完全分开,像是在刻意避免和外界产生任何联系。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结论:这座院子里藏着的,很可能就是他们找了九年的登高一。
2011年4月,花旗国大统帅在克宫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政府和军方的核心人物。
中情局局长把关于阿伯塔巴德院落的情报,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总统,他指着卫星图像上的三层小楼,坚定地说:“大统帅先生,我们有90%的把握,登高一就在这里面。”
大统帅盯着图像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对在场的人说:“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行动方案很快就制定好了——由花旗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精英队员执行突袭任务,他们将乘坐四架黑鹰直升机,从巴铁国的一个秘密军事基地起飞,悄悄潜入阿伯塔巴德的院落,抓住或者击毙登高一。
为了保证行动的秘密性,这次行动没有通知巴铁国政府,甚至连海豹突击队的队员们,直到出发前几个小时,才知道自己的任务目标是谁。
4月29日深夜,巴铁国的夜空像一块黑色的绒布,四架黑鹰直升机像四只无声的蝙蝠,在夜色中低空飞行。
机舱里,24名海豹突击队员穿着黑色的作战服,脸上涂着油彩,手里紧握着突击步枪,每个人的心跳都像擂鼓一样——他们知道,这次任务一旦失败,不仅会让登高一再次逃脱,还可能引发花旗国和巴铁国的外交危机。
直升机飞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阿伯塔巴德的上空。
按照计划,直升机将在院子的屋顶上降落,队员们直接从屋顶进入小楼。
可就在第一架直升机准备降落的时候,意外发生了——院子上空的气流突然变得混乱,直升机的螺旋桨撞到了屋顶的天线,机身失去了平衡,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地坠了下去,最后重重地摔在了院子的草坪上,幸好没有发生爆炸,队员们也只是受了点轻伤。
带队的指挥官当机立断,立刻改变计划:“放弃屋顶降落,全部改为地面进攻!”剩下的三架直升机,迅速在院子周围的空地上降落,队员们像猛虎一样冲了出来,用炸药炸开了院子的大门,然后分成几个小组,向着三层小楼冲去。
院子里的守卫们,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懵了,他们慌乱地拿起枪反抗,可根本不是海豹突击队的对手——队员们的子弹像长了眼睛一样,精准地击中了每一个守卫,几分钟之内,院子里的守卫就全被消灭了。
队员们冲进小楼,一层和二层都没有发现登高一的身影。
他们顺着楼梯,向着三层冲去,楼梯上的灰尘被他们的脚步扬起,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就在他们快要冲到三楼门口的时候,从门后突然射出几发子弹,一名队员的手臂被击中,鲜血立刻流了出来。
指挥官大喊一声:“火力压制!”队员们立刻对着门后开枪,密集的子弹把门板打得千疮百孔。
等枪声停了下来,队员们一脚踹开大门,冲进了三楼的房间。
房间里一片混乱,家具倒在地上,窗帘被风吹得飘了起来。
登高一就站在房间的角落里,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手里拿着一把手枪,眼神里满是凶狠。
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躲在他的身后,吓得瑟瑟发抖。
“放下武器,投降吧!”指挥官用阿拉伯语喊道。
可登高一却像没听见一样,他举起手枪,对着队员们又开了一枪。
这一枪,彻底激怒了海豹突击队员们——他们立刻扣动扳机,子弹像暴雨一样射向登高一。
登高一的身体晃了晃,然后重重地倒在地上,鲜血从他的伤口里流出来,染红了白色的长袍。
他的妻子尖叫着扑过去,却被队员们拦住了。
队员们迅速控制了房间里的其他人,然后对登高一的尸体进行了确认——通过指纹和面部识别,他们确定,这个被击毙的人,就是他们找了九年的全球头号通缉犯登高一。
指挥官立刻拿出卫星电话,向克宫汇报:“目标已被击毙,任务完成!”
克宫里,大统帅和其他官员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忍不住欢呼起来。
大统拿帅起电话,对着电话那头的指挥官说:“干得好,你们为国家立了大功!”这一刻,花旗国终于卸下了压在心头九年的重担,媒体们纷纷报道这个“重大胜利”,民众们走上街头庆祝,仿佛这场漫长的反恐战争,终于迎来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阿伯塔巴德的那座院子里,登高一的孩子们还在哭着喊爸爸;也很少有人想到,击毙登高一,并没有彻底结束班国的战乱。
花旗联军依然驻扎在山地班国的土地上,反美武装的抵抗也没有停止——就像一棵被砍断的大树,虽然主干倒了,可根还在土里,只要有风吹过,就还会冒出新的嫩芽。
几天后,花旗国政府宣布,登高一的尸体已经按照伊斯兰传统,在海上进行了安葬。
可关于这场突袭行动的争议,却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
巴铁国政府对花旗国未经允许就进入本国领土发动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两国的外交关系一度陷入紧张;班国的反美武装分子,则把登高一的死当成了新的动员口号,他们在班国的各个城市发动了更多的袭击,造成了更多的平民伤亡。
花旗国的民众,在短暂的欢呼之后,也开始反思这场战争——他们花了九年时间,付出了无数的生命和金钱,终于击毙了登高一,可班国的局势,却并没有因此变得稳定。
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家庭,依然在承受着痛苦;那些被战火摧毁的村庄,依然没有重建;那些流离失所的平民,依然不知道明天该去哪里。
在班国的山地里,无人机还在不停地盘旋,它们的摄像头对准了每一个可疑的目标,导弹时不时会从天空中落下,炸平一座座房屋。当地的牧民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声音,他们会在导弹落下的时候,抱着自己的孩子,躲进山洞里,等硝烟散去后,再出来收拾被炸毁的家园。
他们不知道这场战争还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
击毙登高一,就像花旗国在班国战争中打了一场漂亮的“局部战役”,可这场战役的胜利,却没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走向。
花旗国依然陷在山地班国的泥潭里,无法自拔;班国人民依然在战火中挣扎,看不到希望。
而那座位于阿伯塔巴德的院落,在被搜查完毕后,就一直空着,院子里的草坪上,还能看到直升机坠落时留下的痕迹,像是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提醒着人们这场战争的残酷与荒诞。
时间会慢慢冲淡人们对这场突袭行动的记忆,可班国的山地不会忘记,那些在战争中逝去的生命不会忘记,那些饱受战火蹂躏的平民也不会忘记——他们记得花旗联军的直升机轰鸣声,记得无人机导弹爆炸的火光,记得失去亲人的痛苦,也记得自己对和平的渴望。
而花旗国,在庆祝完这场“胜利”之后,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击毙一个登高一容易,可想要真正结束班国的战乱,想要在这片土地上实现所谓的“和平与民主”,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甚至可能,这条路根本就不存在。
登高一的尸体在海上安葬的消息传开时,班国东部的楠格哈尔省正下着一场罕见的暴雨。
雨水像无数根冰冷的针,扎在反美武装战士们的脸上,他们聚集在一个潮湿的山洞里,借着微弱的煤油灯,传阅着一张印着登高一头像的传单。
传单上的字被雨水打湿,晕成了一团团黑色的墨迹,可没人在乎——他们只是盯着那张熟悉的脸,有人红了眼眶,有人攥紧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战士,用粗糙的手指抚摸着传单上的头像,声音沙哑地说:“他走了,但我们的仗,还得接着打。”
这话像一颗火星,点燃了山洞里所有人的斗志。
第二天清晨,雨刚停,楠格哈尔省的公路上就响起了爆炸声——反美武装在一座桥梁下埋了炸药,把花旗联军的一支补给车队拦在了半路。
车队里的士兵们还没反应过来,山上就冲下来一群拿着步枪和火箭筒的反美武装战士,子弹像飞蝗一样掠过路面,打在装甲车的钢板上,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花旗联军的士兵们躲在车里还击,可反美武装战士们借着路边的石头和树木掩护,打得又准又狠,不到半个小时,就把车队里的三辆卡车炸成了废铁,还缴获了满满两车的弹药。
这场袭击,像是一个信号,拉开了班国反美武装“复仇行动”的序幕。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班国的各个省份都爆发了针对花旗联军的袭击:坎大哈省的联军基地遭到火箭弹袭击,虽然没造成人员伤亡,却把基地里的士兵吓得一夜没敢合眼;赫尔曼德省的一个联军检查站,被反美武装用自杀式炸弹袭击,五个花旗国士兵当场死亡,检查站的岗楼被炸得只剩下一堆断壁残垣;就连相对平静的喀布尔郊区,也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炸弹在一家联军经常光顾的餐厅门口引爆,造成了十几名平民伤亡。
花旗联军被这些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焦头烂额,他们原本以为击毙登高一后,反美武装会群龙无首,不攻自破,可没想到,这些抵抗者反而变得更加凶猛。
联军指挥官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下令加大对班国山区的“清剿力度”,派出了更多的无人机和直升机,对着可疑的山洞和村庄狂轰滥炸。
那些日子里,班国的天空几乎看不到蓝色,到处都是无人机盘旋的“嗡嗡”声,导弹爆炸的火光像一朵朵丑陋的蘑菇,在山地间此起彼伏地绽放。
有一次,花旗联军的情报部门收到消息,说楠格哈尔省的一个村庄里藏着反美武装的头目。
他们没有核实消息的真假,就立刻派了三架无人机,对着村庄投下了十几枚导弹。
导弹落下的瞬间,村庄里的房屋像积木一样倒塌,尘土和火焰冲上天空,连几公里外都能看到黑烟。
可等地面部队冲进去搜查时,才发现村子里根本没有反美武装,只有几十具平民的尸体——老人、妇女、孩子,横七竖八地躺在废墟里,有的孩子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烤饼,脸上还带着惊恐的表情。
当地的牧民们听到消息后,拿着铁锹和锄头,愤怒地冲向联军的基地,他们对着基地的铁丝网大喊:“还我们亲人!还我们家园!”可基地里的士兵们,只是端着枪,冷漠地看着他们,甚至有人朝着天空开枪,试图驱散人群。
牧民们的愤怒,像被冷水浇灭的火焰,慢慢变成了绝望——他们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对抗强大的花旗联军,只能默默地回到被炸毁的村庄,把亲人的尸体埋在废墟旁边,然后带着剩下的家人,逃到更深的山里。
花旗国国内的媒体,很快就报道了这次“误炸平民”事件。
照片上,废墟里的孩子尸体让无数花旗国民众感到震惊和愤怒,他们纷纷走上街头,举着“停止杀戮”的标语,抗议政府在班国的军事行动。有议员在国会上质问国防部长:“我们到底在班国做什么?我们是来反恐的,还是来屠杀平民的?”国防部长低着头,支支吾吾地说:“这只是一次意外,我们会加强情报审核,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可这样的承诺,在一次次的“意外”面前,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
中情局也因为这次事件,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指责。
人们开始质疑,他们当初是怎么确定阿伯塔巴德院落里藏着登高一的?会不会也是一次“误判”?中情局局长为了平息质疑,不得不召开新闻发布会,展示了更多关于登高一的情报——包括他在院落里散步的视频截图,以及他和家人的通话录音(虽然录音里的声音模糊不清)。
可就算这样,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有人甚至猜测,花旗国政府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故意“伪造”了击毙登高一的事件。
这些质疑,像一块巨石,压在花旗国政府的心头。
他们原本想靠击毙登高一,提升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可没想到,反而引来了更多的麻烦。
为了挽回局面,政府决定加大对班国的“援助力度”,承诺出资重建被炸毁的村庄,为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
可这些承诺,大多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大部分援助资金,要么被花旗国的企业截留,要么被班国伪政府的官员贪污,真正能落到平民手里的,少得可怜。
在班国的首都喀布尔,有一家由花旗国援助修建的医院,医院的外墙刷得雪白,门口挂着“花旗国-班国友好合作项目”的牌子,看起来光鲜亮丽。
可走进医院里面,却是另一番景象:病房里的病床破旧不堪,有的连床垫都没有;药品架上空空荡荡,只有少数几种常见的感冒药和消炎药;医生们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手里拿着用了十几年的听诊器,面对病人的痛苦,只能无奈地摇头。
有一次,一个孕妇因为难产被送到医院,可医院里没有麻醉药,也没有专业的助产设备,医生只能用一把生锈的剪刀,在没有消毒的情况下为孕妇接生,最后孕妇和孩子都没能活下来。
孕妇的丈夫抱着妻子和孩子的尸体,在医院门口哭了整整一天,他对着医院的牌子大喊:“这就是你们说的援助?这就是你们带来的希望?”
这样的场景,在班国随处可见。
花旗国的“援助”,就像一件华丽的外衣,掩盖不了班国人民的苦难。反美武装也抓住了这一点,他们在班国的各个角落散发传单,上面写着:“花旗人带来的不是和平,是战争;不是援助,是掠夺。他们杀死了登高一,却杀死了更多的平民。
站起来,和我们一起,把花旗人赶出我们的国家!”这些传单,像一颗颗种子,在班国民众的心里生根发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反美武装,有的甚至是曾经支持过花旗联军的平民。
花旗联军的士兵们,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以前,他们在班国的村庄里巡逻时,还能看到村民们怯生生的笑脸,偶尔会有人给他们递一杯热茶;可现在,村民们看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仇恨,有的甚至会朝着他们扔石头。
有个士兵在日记里写道:“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侵略者,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讨厌。
我开始怀疑,我们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真的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吗?”
这种怀疑,像一种传染病,在联军士兵中蔓延开来。
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始厌倦战争,他们想念家乡的亲人,想念家里的沙发和电视,想念没有炮火和枪声的日子。
有一些士兵,甚至因为受不了战争的压力,选择了自杀——在2011年,花旗国驻班国联军的自杀人数,比战死的人数还要多。
这些自杀的士兵,有的在遗书中写道:“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梦见那些被我杀死的平民,他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我受不了了。”
花旗国政府为了防止士兵们的士气进一步低落,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给士兵们增加薪水,延长假期,甚至派心理医生到基地为士兵们做辅导。
可这些措施,根本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士兵们的士气,还是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路下滑。
在班国的山地里,无人机还在不停地飞行,导弹还在不停地落下,可反美武装的抵抗,却越来越顽强。
他们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不管花旗联军怎么清剿,都无法彻底消灭他们。有一次,花旗联军对一个反美武装的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动用了直升机、坦克和装甲车,把据点所在的山头炸得面目全非。
可等他们占领据点后才发现,反美武装早就转移了,只留下了几个稻草人,上面穿着反美武装的衣服,用来迷惑联军。
联军指挥官看着那些稻草人,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自己又一次被反美武装耍了。他对着手下的士兵们大喊:“我们到底在和什么样的敌人打仗?他们到底藏在哪里?”可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反美武装就像班国山地里的风,看不见,摸不着,却能随时随地给联军带来麻烦。
击毙登高一后的第三个月,花旗国政府宣布,将从班国撤军一部分士兵,理由是“班国的安全局势有所改善”。
可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政府的借口——他们是因为承受不住战争的压力,才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那些被撤回国内的士兵,虽然回到了亲人身边,却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生活——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战争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每天都活在恐惧和痛苦中;有的甚至因为无法适应和平生活,选择了再次参军,回到那个让他们既憎恨又无法逃离的战场。
而留在班国的联军士兵们,依然在重复着每天的巡逻、清剿和战斗。
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里待多久,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
他们只知道,班国的山地里,每天都会有新的冲突爆发,每天都会有人死去,而他们,只是这场漫长战争中的一颗棋子,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在阿伯塔巴德的那座院落里,杂草已经长得有半人高,院子的围墙因为无人维护,已经出现了裂缝。偶尔会有附近的孩子,翻墙进入院子里玩耍,他们在草坪上追逐打闹,捡起地上的小石子,扔向那栋早已空无一人的三层小楼。
对这些孩子来说,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废弃院落,他们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震惊世界的突袭行动,也不知道,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鲜血和仇恨。
山地班国的天空,依旧被无人机的阴影笼罩;班国的土地,依旧被战火蹂躏。
击毙登高一,就像一场短暂的烟花,虽然在夜空中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却很快就消失在了黑暗中,没有给班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和平,对班国人民来说,依然是一个遥远而奢侈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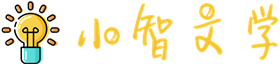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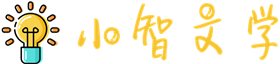 小智文学
小智文学